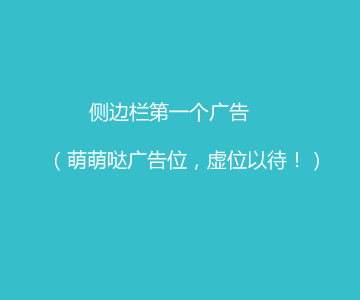这是一篇从小我私家履历出发,动员学理思索的文章。母职问题,是女性主义的难题。关于是否要做母亲、若何明白母职,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相关身份与职责,从来都是争执不下、难有效果,但又真实存在的问题。黄微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青年学者,若何处置这个问题,也曾让她陷入生涯的疲劳,与知识上的某种逆境(现成的女性主义理论也难给予现成的谜底或框架)。但她仍在理论探索中,梳理了女性与生育的某种线索,也对经典性的讨论做了归纳与对话。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念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原文题目:《《念书》新刊 | 黄微子:想象一种女性主义的母职》,公布在《念书》2021年2期新刊。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有关母职和女性主义的讨论经常是极端撕裂的。一方面是舞蹈家杨丽萍由于未曾生育而被斥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另一方面是网络红人 papi 酱在母亲节当天晒出怀抱婴儿面带倦容的照片而被质疑孩子“随父姓”,甚至被诅咒为所谓“婚驴”。
母职和女性主义好像是二元对立的话语,贤妻良母和自力女性好像是势不两立的主体。这种认知,不仅存在于一样平常的网络言论中,有时也体现在一些知识女性的文章里。我是一名知识女性,学习和解说文化研究。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身份令我自有身之日起就在批判地反思母职,也反思女性主义内部关于母职的对话。
papi 酱在2020年5月10日母亲节当天发了上述微博,随后受到部门网友攻击
生育对于我的打击比我以往生掷中任何一个事宜都大。
在第一次临盆以前,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是一个全情投入母职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被外界以为是异常传统的南方小城潮州。我小时刻,我妈一面亲力亲为地照料我们姐弟四人的生涯,一面和我爸一起打理小生意。总的来说,我们家亲子关系融洽,子女学业有成,然则,我们并不以妈妈为楷模,由于她看上去过于劳碌,又缺乏属于自己的事业。
受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我一直视受社会认可的小我私家成就为更高的人生价值。甚至连我妈也没计划将我们几个女儿再生产为“贤妻良母”。作为家中的长女,我一路由着自己的兴趣念到了博士。我并不太喜欢小孩,甚至在妊娠十月的时刻,我先生问我说:孩子生出来后你不会母爱爆棚吧?我还言之凿凿地回覆:不会。
然则,当大女儿脱离我的子宫、来到我眼前的那一刻,事情起了转变。我真真切切地成为一个母爱满溢而出的妈妈。我云云爱谁人搁在我肚皮上湿漉漉暖乎乎的婴孩,以至于愿意为她蒙受一切。甚至由于她的存在,我以为有需要“重估一切价值”。我一直实验明白自己的这种转变。这是我这些年来关切母职研究的直接念头。
我虽然不相信这是出于所谓女人的天性(生物决议论),也不能满足于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对于母职的指认——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效果。我最先反思这种身体与精神、生物与文化、情绪与理性二分的注释框架。
我固然不以为女性由于拥有子宫便自然拥有相同的身体履历,却也不能认同那种完全否认心理差异的性别理论。我们的文化会引领我们对身体的感知、命名和叙述,我们的身体履历也会令我们谨记或反抗身处的文化,它们是相互天生的。以是,我注定无法将我何以马上成为一个醉心于母职的妈妈归因于任何单一变量——激素、或爱欲、或责任。
自然临盆时,新生儿经常会被放在母亲身上剪脐带
英国小说家卡斯克(Rachel Cusk)说:“我做母亲时,以为之前从未有人写过若何做母亲。”但从她的非虚构作品《成为母亲》引经据典了许多形貌有身和生育的文学作品来看,事实上并非没有人写过,而是这些形貌很难引起没有母职履历的读者的注重。
有关母职履历的讲述和誊写,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到公共讨论之中。
一个饱读诗书的年轻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前,也对有关母亲的形貌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卡斯克异常有受众局限性的自觉,她说:“一本讨论母性(原文是 motherhood)的书只能吸引其他母亲;纵然是母亲,也只能吸引像我这样的,她们以为做母亲的履历异常主要,以致阅读相关读物能给人某种新鲜的慰藉。”“由于险些无法对外界注释做母亲的体验。”“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子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
《成为母亲》中译本封面
若何看待母职,向来是女性主义的难题。波伏娃视母性为将女人酿成仆从的手段,正是今日中国“不婚不育保平安”主义者的精神泉源。而一部门女性主义者,如吕频,提出“作废母职——作废这个作为父权制之基的女性义务角色,住手无酬劳动和被牢固住的情绪模式”的主张(《代孕即将合法化了吗?令人焦虑的母职买卖》),则是这种思想从小我私家选择上升到社会制度放置。
而一个自认追求性别平权的女性生儿育女之后,在母性即是守旧、母职只是榨取的“女权”叙述中,无法安置自身的履历。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她们否决母职,即是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宗教右翼。而今天,海内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敌视已婚已育女性的态度,实在是通盘接收了父权社会对母职的叙述,即是把对家庭、婚姻和生儿育女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女德班”。
为生孩子而牺牲康健、事业,甚至献出生命的女性没有获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同情。由于她们不相符工具理性原则,通不外世俗利益的成本收益核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〇一六年就职中科院的科研事情者杨冰在孕中期因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住院治疗时代猝死。最初由于家族疑似“医闹”而成为热点新闻,但迅速地,舆论的焦点转而指摘杨冰死得不值,是父权体制的受害者。
肖慧在谈论这个新闻时,在揭破所谓“母性神话”后,作出这样的总结:“讨论女性甘冒生命风险选择生育是否出于自主意愿就没有太大意义,由于我们以为自己所拥有的小我私家意志和选择自由实在是已经被意识形态规范化了的意志和自由。”(《女性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价值完成母职?》)
女性在生育中事实有没有能动性?母职在女性的小我私家生掷中有没有积极意义?母职有没有社会价值(并非以父权社会的坐标来权衡),或者我们敢不敢想象一种逾越小我私家自由的社会价值?这些是我成为母亲之后一直盘旋在脑际的问题。
女性事实可不可能有生育的自主意愿?若是我们看一些超出异性恋婚姻家庭模式的例子,也许对照容易找到谜底。在男性缺席的情境下,借精产子的独身妈妈或性少数妈妈的自主生育意愿也许不难获得确认。就算是回到通俗女性的一样平常生涯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瞥见那种坚贞、有主见的妈妈。
梁小岛的书里(《有时是爱,有时是忍耐——全职妈妈的故事》)采访到一位名叫 Lily 的女性,二胎怀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儿,不幸的是, B超检查发现,左边的胎儿已经夭折,受夭折的胎儿影响,右边的胎儿有可能智力和发育不健全。在丈夫、公婆甚至自己的妈妈都主张放弃的情况下,Lily 仍然决议生下孩子。
书中讲述了生涯在香港的十位全职妈妈的故事
简朴否认女性的自主生育意愿是异常轻率的。借用雷蒙·威廉斯的话,这种完全被母性神话洗脑的母亲并不存在,“她们是被二流的社会剖析编造出来的”(‘they are the bad fiction of our second-rate social analysis’,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这一类视生育为地狱、视生育意愿为被操作的看法,进一步割裂了女性。冷笑为生育支出大价值的“失败”母亲,主张“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靠自己的”道德提高主义,跟那种歧视“大龄剩女”、训斥不育女性的道德守旧主义,至此殊途同归,造成差别女性群体之间的敌意和倾轧。
这种境况,现实上是现代资源主义公私领域星散的结果。现代资源主义的生长使得生产移出家庭,生产的空间成为了公共天下,栖身的空间被界说为私人天下,由此形成了公共生涯与家庭生涯的二元对立,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育儿和家务劳动被贬低为非生产性的劳动,公共价值凌驾于家庭价值之上。
不少女性主义者现实上接受了这种价值设定。她们的解决方案是女性要和男性一样,去争取公共天下的角色、成就和夸奖。故障女性从事公共生产,或者使得女性留在了家庭生涯的心理特征,好比子宫和生育的能力,则被视为贫苦。
杨冰猝死之以是成为热点新闻,其中一个原因是单元公文透露出来的身份——“中科院理化所青年科技主干”。而以为她死得不值的舆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身份,“大好前途的科研人才却死在生孩子上。”
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形成的职业理想,并不包罗母亲一职。我们知道许多职业的风险,而由于这些职业风险支出的价值,在公共天下中可以享受高尚的讴歌。但我们不知道成为母亲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成为母亲有怎样的风险。
居里夫人由于研究放射性物质而死于血液病,我们感念于她的牺牲。杨冰女士由于有身而死于并发症,舆论则挖苦她的愚昧。殊不知,纵然在今天,孕产妇殒命仍然是一个异常一样平常和真实的威胁。若是我们把“母子平安”当做常模(norms),则会对那些生产不顺的“误差”母亲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是污名。
制造差别女性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是父权资源主义屡试不爽的计谋。而哪一个女性群体可以在父权资源主义社会获得更大的话语优势呢?“贤妻良母”太传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女权太老土,相较之下更富经济资源(消艰苦)和数据资源(流量)的年轻、漂亮、肯花钱、会服装、性解放的女性更能抢占“女权主义”的高地。她们是新自由主义的主体。为人母者想获得这种“女权主义”的接纳,只能是通过时尚消费和身体治理,以掩饰生过孩子的身体出现,乞求一个“辣妈”的头衔。
2013年热映电视剧《辣妈正传》
一个好的系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系统。它应当允许差其余母职实践。女性整体固然不是无差其余,相反,是由许多处于差其余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女性群体配合组成的。
就个体层面而言,不婚不育固然是一种正当的可选项,但不能反过来以为它是一种更提高、更优的选择。不能把为生育支出大价值的母亲想象成提线木偶,或者让有康健风险的女性失去做母亲的权力。社会应当提供情绪、物质、知识和手艺支援,以令生育加倍平安和少痛。
有的女性主义者留意于生殖科技来解放女性。为此,吕频设想了一种十分科幻的方案——人造子宫。她以为《优美新天下》和《黑客帝国》对人造子宫的恶心描绘是父权制的一种虚伪陈述。
在我看来,留意于人造子宫的设想,临时岂论其现实可能,是一种无邪的手艺乐观主义——依赖手艺作为一种缔造一致、协作的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问题是:第一,人造子宫是否还需要人类女性的卵子?若是需要,取卵的历程需要女性支出不少时间、精神和心理的价值,与男性取精的历程绝不一致。第二,人造子宫的运作是否还需要人类劳动的介入?婴儿从人造子宫临盆出来之后是否还需要人类劳动的介入?若是需要,什么人对照可能被分派到这样的岗位?
影戏《黑客帝国》中的人造子宫
就当下已经生长出来的生殖科技而言,首先,它是一件昂贵的商品,不能令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受益。生殖科技不能替换女性生育,在现在的手艺条件下,它只能让其余女性来替换基因或执法意义上的母亲举行有身和临盆。
这和奶妈、育儿嫂一类署理母职是类似的,通常由居于经济文化优势的女性转移到居于劣势的女性身上,并没有促成女性整体的解放。这实在反映了母职的社会评价不高,由人力资源回报低的女性替换在公领域中从事“更有价值的事情”的女性,或让中上阶层的女性可以享受闲暇。
这进一步导致了全职妈妈的被贬低。我们的表征系统出了问题。一方面是对所谓母性的讴歌,一方面是对家庭妇女的嫌弃,这种嫌弃渗入无意识之中。全职妈妈并非什么都不做。许多人除了独力照顾小孩(可能不止一个)和打理家务,还会做一些兼职、在家事情甚至创业。她们缺少的不是小我私家价值,而是社会认可。
这种社会认可的缺失,导致了少女时代的我对我妈的不认同和对母职的拒绝。潮汕女子听说都是“贤妻良母”。以前,每当有人听说我先生娶了一个潮州人而羡慕他“有福气”时,我实在稀奇不服气,对这种刻板偏见深恶痛绝。由于在整个妇运史中,“贤妻良母”是被污名化的,民国时期的“新贤妻良母主义”也常被斥为“复古逆流”。
然而,成为母亲之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两难田地。你要么保持自力姿态而不做“贤妻良母”,但多数对丈夫和孩子(重点是孩子)怀有亏欠之情;要么为了相符主流社会对“贤妻良母”的传统期待而牺牲自我。
我重读有关“贤妻良母”的文献,稀奇注重到周恩来总理在1942年写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他以为“贤妻良母”作为一个牢固搭配,其所指已经连结上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在,甚至于在前面冠以“新”字也不能排除这种连结。
不外,“我们非空口否决‘贤妻良母’,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央的新看法,来取代‘贤妻良母’的旧看法的。”“妇女于尽母职的时刻,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分工的必须。但我们否决捏词妇女应尽母职,因而作废其社会职业,便其陷于更大的难题,转致故障母职。我们更否决以同样捏词不认可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外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而已。”1942年,周总理就提出要给家庭妇女以一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贬低家庭妇女,则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无疑了。
周恩来在1942年写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霸权不只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固然也有物质的面向。但我们否决那种经济决议论,以为女性有了自力经济泉源,便可以解决一切性别一致问题;或者以为达至性别一致的条件,是女性要有受薪的职业。
那些放弃了职位甚至高薪的妈妈,她们确实需要让渡一部门权力,但并不是悲苦无助的。相反,她们有更多的空间来反思消费主义和资源主义的事情伦理。“一小我私家的收入就可养全家,另外一小我私家就可以做一些与钱无关的、有意义的事情。”(梁小岛书中全职妈妈 Fiona 的话。)
我想象的女性主义母职,首先是通过一种葛兰西式的路径,重新界说母职。葛兰西以为,旧的文化霸权虽然壮大,但并非坚如盘石,我们需要在“知识”层面为争取新的“赞成”而战,这是一种阵地战(war of position)。详细到否决男权意识形态的斗争,没有一种整体方案能够切实而彻底地推翻所谓“母性神话”的霸权。我们要做的,是在社会文化中确立一种新知识:母职是与一切公领域的事情一样有意义、有价值的。它不是一种次等的劳动。但这不是要强制所有女性从事一致强度的母职劳动。女性可以在她自身所处的情境中,决议推行母职的方式和介入水平。
我们固然可以是自力的贤妻良母,可以是有主见的贤妻良母,可以是介入家庭决议的贤妻良母,可以是介入公共事务的贤妻良母。当我不再为道德提高主义一叶障目的时刻,我终于可以认可,我妈在生儿育女的历程中,在家庭经济的治理上,充满了能动性。她不是刻板印象中那种旧时代的家庭妇女,她是新时期的贤妻良母。她获得了她想要的人生。
其次,女性主义母职不是完全由母亲个体来负担的。公共机构、女性整体和家庭内部的支持网络同样异常主要。父亲推行父职是女性主义母职得以实现的主要基础。以为父亲不认真推行父职是由于所谓“母职守门”(母亲通过设立严酷的家事尺度来限制父亲对家事的介入),或以为父职是一种比母职更理性、科学因此更高级的亲职实践,都是有问题的(这个值得另文讨论)。父职和母职并不应该有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牢固分工,而应由父亲和母亲个体基于自身情境天真分配。
女性主义者岂论是争取对母职的正面表征,照样在一样平常生涯中践行母职,都是一种历久的、有机的介入,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
* 文中图片未注明泉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公布于《念书》2021年2期新刊,作者:黄微子。更多文章,可订阅购置《念书》杂志或关注微信民众号:念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html/2021/0416/4318.html
- 上一篇:华宇物流网点查询_出海东南亚,我们划了以下重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