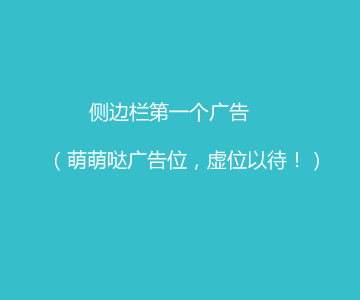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谷雨设计-腾讯新闻(ID:guyuproject),原题目《安小庆:若何把已经写滥的选题只管写得“坦荡”》,作者:安小庆,题图来自:原文
“虽万般不舍,然生涯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6月,一位因疫情影响准备返乡的农民工,在东莞图书馆写下了这样的留言。他叫吴桂春,在东莞17年,其中在图书馆看书12年。这则留言传开之后,感动了许多人,吴桂春也因此找到了新事情。
7月,《人物》杂志作者安小庆关于吴桂春的特稿《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问世,并获得了当月的谷雨公益写作奖。在文章中,安小庆写到了吴桂春和他这一代农民工,写到了东莞图书馆,也写到了东莞这个天下工厂和它背后的珠三角。“这篇文章是现在‘被小看’的资本主义森林里的微光,也是遥远已往的回响。”谷雨奖评委杨潇如是说。
对吴桂春前后做了三次采访
这个选题是编辑赵涵漠先生派给我的。故事发生在东莞,离我平时常驻的深圳很近,高铁已往是17分钟。但接到题时,我还在外地休年假最后一天。那时的媒体报道大部门都是两三分钟的视频,截面性地讲了那两三天发生了什么,吴桂春说了什么,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到东莞找吴桂春的时刻是7月初,他自己已经无法自由决议是否接受采访,任何采访都要经由当地宣传部门和他公司的批准。我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批准。吴大叔本人是可以接电话的,他告诉我,若是我得不到采访允许,他也可以在电话里跟我聊聊。但我照样希望找到其他突破的方式。
《南方都市报》的一位前同事提供了辅助。他告诉我吴大叔现在事情单位的向导电话,他住的员工宿舍在小区几号门岗的劈面。此前,由于“农民工留言图书馆”是件“正能量的好人好事”,东莞一家公司给吴大叔提供了新的事情,公司客观上有自我宣传的需求,那位向导人也蛮好的,体贴我交不了稿会很忧伤,准许第二天中午把吴大叔带出来一起吃顿午餐,午餐的一个小时可以聊一聊。
采访一共做了三次。第一次是用饭的时刻;第二次是吃完饭又争取了一个多小时,采访地址是在小区物业公司的办公室。这两次采访旁边都有许多人,而且一直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打过来联系采访,许多细节的问题没办法睁开。我以为他这种忙碌和被严酷牵制的状态最少还会连续一周,就有意识地和那些采访错开了三四天,先去做其他部门的采访。
我们不想做一个拼时效性的稿子,而已经有的报道,从内容和气概来说都很乏味。从信息量来看,重复。从人物来看,扁平。从文字来看,没有故事发生地的空气。好比许多报道里写他看过什么书,通通都是《左传》《春秋》《红楼梦》。但提问和回覆都只到了书名,余下就没有了。在急急的电话约访或者视频拍摄内里,记者也很难跟一个采访工具说,我们来聊一聊念书的详细细节,或者聊聊我们相互都对照有共识的文本。
以是我在想,只要有时间和机遇能让我跟吴大叔坐下来聊,我一定可以问到很细节的、很有分辨率的器械。因此,等其他部门的采访完成之后,我直接去吴大叔的宿舍跟他聊了四个小时,这是对他的第三次采访。
吴桂春在他做绿化事情的小区 图丨人民视觉
不包罗写稿,我在东莞待了一周。在去东莞前,我差不多对稿子的偏向有了一些基本的想象。包罗我和编辑漠漠的电话沟通里,我们险些是有一个心有灵犀般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个稿子想要搞清楚三个问题:为什么故事发生在吴桂春身上?为什么故事发生在东莞图书馆?为什么故事发生在珠三角?
以是稿子的切入点或者视线有三层:第一层是吴桂春,吴桂春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暮年农民工群体。第二层是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和它所在的公共图书馆行业。第三层是都市,东莞这个落脚都市、天下工厂和它背后的珠三角。
稿子发出后,不少偕行和读者告诉我,他们以为这篇稿子写得对照“坦荡”。我想可能是我们面临一个猝然泛起的网红事宜时,没有驯服地把这件事当做一件“自然”发生的事,而是好奇地发出许多疑问。
这些疑问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米尔斯说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当面临这个选题的时刻,不是只想到个体的生计是何等不容易、何等的苦情,或者“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固然,这些偏向都没错,但还不够。已往突发报道里,通常是写一小我私家的家庭环境、生长历程、小我私家性格和他所做的决议之间的关系。只写一小我私家的心灵史和生长史,照样有点单薄。
然则,这部门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许多报道里,我看到的细节都很相同,而且严酷来说只是一种概述,算不上细节。以是第三次采访的时刻,我问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好比,你在鞋厂使用的劳动工具叫什么?鞋厂的味道是怎样的?每年花若干钱买衣服?在那里买?手机套餐是若干元包月的?没有回老家的时刻,在东莞怎么过年?每个月怎么给儿子打生涯费?这些年的人为收入有什么转变?迁居的时刻,哪些器械一直随着你?
我印象对照深的细节之一是,我问他每年花若干钱买衣服,他说不到一百。广东虽然没有北方严寒,但最冷的时间照样需要穿羽绒服的。以是我问他,每年买三套热天穿的衣服之外,冬天不穿羽绒服吗?他说在东莞挺挺就已往了,不需要买。我问,那有几年你回家过年了,湖北很冷,回去穿什么衣服呢?他说,他穿他哥哥或者弟弟的厚衣服,回来要上车的时刻就脱掉,还给亲戚。回去穿上、走时脱下,这种即穿即脱的画面,让我想起社会学家项飚说的那种“悬浮”和暂且感。这跟都市人包罗我自己在内的那种黏着、膨胀物欲,是完全差其余。
另有许多细节,是通过无目的的游荡和漫谈得来的。我曾去吴桂春之前事情的鞋厂楼下的快餐店坐了一小时,吃了一碗面。快餐店老板娘是从四川来东莞的,开店跨越20年,她体恤工友,看到体力劳动者,会多抓一把面条下锅。包罗老板娘,另有鞋厂的绝大部门工人,很多若干都是90年月出来打工的大姐,在东莞打拼了二三十年,她们的生命是以来东莞作为分界点的。她跟我讲她在东莞的迁徙史,讲她和大儿子的生疏,讲自己劳碌了半辈子,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她就回老家。
等我去了鞋厂,我发现鞋厂的工人险些也都是中暮年人。谁人鞋厂给我的打击异常大。我经常在新闻或者同伙的讲述里听到,机械人已经在珠三角的工厂里取代了若干比例的流水线工人,这是很有未来感和提高自信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我随着温州老板走到二楼那间厂房,我感受我时空穿梭到了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
“图书馆留言”事宜前,吴桂春事情了七年的鞋厂
谁人鞋厂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手事情坊。在那里的大半天,我和许多工友谈天,没有人懒惰和放弃过生涯,每小我私家都竭尽全力了,可是随着青春流逝,他们一步步从大厂被筛选,流落到小厂,再流落到这种不交五险一金的小作坊。那天的采访里没有吴桂春,然则其他大龄外来务工者的故事,也是他故事的一部门。
包罗每次打车,我都市跟司机谈天,最后发现好几个司机以前都是给港商或者台商开车的,这两年不景气,这些工厂或者倒闭,或者搬去东南亚了。
另外,走在东莞的街上,我感受年轻人少了很多若干很多若干。我以前来过东莞,也在佛山事情过两年,那时我对珠三角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走在镇街的商业中心,你的眼前有无数双年轻人的大腿在迈动。我会感受到作为“天下工厂”的东莞,没有过往那么躁动了。这种空气提醒我,好比郑小琼和吴桂春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东莞的,然则由于时间节点的差别,这些故事就有差其余气温顺温度。
包罗脱离东莞的前一天,我去了老城区一家很著名的饭馆,内里播放的照样罗文唱的粤剧。岂论国际局势、机械大工业和流水线怎么转变,有一些器械也许是稳定的。这其中许多器械虽然可能最终落不到稿子内里,然则我以为我们要浸泡在内里,获得一种靠山性的存在,有些部门或许最终不写,然则在我们需要一些判断或者做一些形貌的时刻,我能从影象里抓取到总体性的空气。
两个没放进去的细节
在个体故事这一层的采访上,实在那几天,我考察到了许多关于一小我私家在伟大的运气调转时刻,他正在履历的许多魔幻现实。但一篇稿子负担不了所有的功效,写稿的时刻,我舍弃了挺多。
好比,吴大叔说,他在东莞的17年里,买水果的钱不跨越40块,这个细节其余媒体写过,但我总是不相信,以是最后那次采访,我又问了一遍。
我那天去找他,也提了一些水果去,他显示得异常抵制,险些是要冒火的样子。可能正是由于近二十年没有消费水果的习惯,他会以为几袋水果在炎天是很贫苦的,会坏掉。经由许多年一小我私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涯之后,他不会来中产阶级的那套审慎礼貌与虚与委蛇,不会说谢谢你上门还带器械,反而是你给他带来了贫苦。
那时我建议,吃不完的话,送给其他的工友吧,他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似乎也不需要拿水果去生长或者维护一段社会关系,这种生计是暂且性的。就像项飚先生说的“悬浮”。这些都是我的考察,没有写到稿子里去。最后他还拿了一半水果让我带走,我不拿,他蛮生气的。
需不需要在稿子里出现对吴桂春的立体、周全形貌?有同事问过我,我写稿前也思量过这个问题。我那时只有一种直觉,就是在叙事上,我不想要一个朦胧的、对一小我私家的周全形貌。我想要的是一张有景深的照片,或者一幅透视的绘画。我要完成的不是以吴桂春为工具的人物特稿,我要完成的是以他为远景,但在最远景的人物背后还存在差别景深的一张照片。若是在这张照片里对人物面面俱到,焦点反而模糊了。
《新华字典》是吴桂春这些年翻得最多的书
关于最远景的人物,我采到了不少之前没有看过的信息,也获得了许多有意味的细节和场景。但既然这不是一篇人物特稿,那么,在这个文体中,若是试图去形貌人物的立体和庞大,我会以为这是对采访工具的不公平。或许时间距离再拉长一些,用一篇专门的人物特稿来写吴桂春,是合适和公允的。
以是在文章的第一部门,我只形貌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涯和他伶仃的生计状态。这是所有人都有的共识,但很少有写得稀奇细节的。若是我是读者,我会希望你给我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复的判断和笼统的形貌。
有一个故事忘了放进去,挺惋惜的。有一年年底放假前,鞋厂老板请人来翻修厂房,吴桂春和装修工人由于灰尘的问题发生口角,装修工人说,你有本事的话,也不会在这里打工了。吴桂春异常生气,摒挡器械就走了。老板劝他干到放假再走,说别人在灰尘里都可以做,怎么就你不行。他连人为都没结算就走了。等越过春节,他再来找工的时刻,才从老板那里拿到上一年最后一个月的人为。
从这件事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自尊很强、很有个性的人。若是读者知道这个故事,也许能够更明了他干嘛要和林黛玉的鹦鹉较量。我们也能从这个故事里看到,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是厚实多样的,老板不是新闻里总泛起的血汗资本家形象,这位来自温州的小企业主和外来务工者之间,既是劳资关系,又有同是天涯揾食者的小小义气存在——并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做到把人为分文不少地再给工人的。也有工人提到,他们急用钱的时刻也可以找老板借。每个月也是这位老板帮吴桂春把生涯费转给儿子。
“这个故事,或许只能发生在东莞图书馆”
在最远景的人物采访背后,是东莞图书馆和它代表的公共图书馆行业。在去东莞前,我唯一专门做的作业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部门。我以前还挺喜欢看关于“都市研究”的书的,也写过关于“公民修建”的稿子。都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的政治。以是在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刻,我会想到图书馆的公共性这一点,也有意识地去查了许多“公共图书馆”的资料,好比它在工业革命泛起后的生长历史,包罗它在中国的历史。
很有趣的一点是,我发现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已往20年里,曾经三次在节目里提到公共图书馆。最近一次就是在连线东莞图书馆的时刻,之前两次分别是谈论“杭州图书馆事宜”和更早的时刻他去美国采访波士顿图书馆,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公共图书馆。
这其中对我打击异常大的,就是从千禧年最先,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行业险些是举行了一场自我革命。许多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图书馆从业人员在重申和实践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力争去做彻底的变化。其中一些文献里就提到了东莞图书馆的实践,和馆长李东来对图书馆“以文养文”这种行为的指斥,以及他自己对“公共性”的一些论述。
东莞图书馆是天下地级市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因此去采访前,这一部门已经是我想要力争去证实或者证伪的主要一部门。在做人物采访的事情里,我有一个履历,就是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重复性。当我在资料或者新闻中看到一个行为,我会想,这个“有时”的背后会有必然性或者行为的重复性吗?放到“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事宜里,许多采访工具都告诉我,若是没有总服务台事情人员王艳君的敏感、共情和敬业,那么吴桂春留言的事也许率不会发生。我会去想,那么王艳君也许率也不会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事。再进一步,若是一个机构的价值观具有稳定性,那么在“网红”事宜发生之前,一定还发生过许多没有被看到或者流传的类似事情。
在图书馆采访的那周,我没有抱着要去做对一道证明题或者论述题的迫切,也许是一种游荡的状态吧,想要以一个通俗使用者的身份去考察这个公共机构。我对王艳君和其他图书馆事情人员的采访也是云云,更多时刻是在看她们若何跟读者互动。
王艳君的事情岗位在总服务台,她也许是整个图书馆语言最多的人。她也是一个很爱跟人打交道、共情心很强的人。和我生涯里看到的许多公立机构事情人员差别,她在回覆读者询问、疑问,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刻异常耐心,她给读者的回覆不是一个封锁的谜底——我是经常由于一个封锁狂妄的谜底而跟人吵起来。她会把能想到的所有解决办法逐一说给你听,告诉你她会偏向哪一种处置,然后由你自己来选择你想要怎样的解决方式。
也是在第二次、第三次的采访里,她讲了许多图书馆的一样平常实践。这些在她看来是寻常的处置,在我听来是很久很久没有在采访中获得的有关人文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暖光。
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好几回提起没有处置好那对因家暴而离家出走到图书馆的母女的事。那件事已经已往许多年了,实际上她们做得已经很好,但她几回提起都很懊恼和悔恨。一小我私家很认同自己的事情,才会一直去反刍自己已往的一个行为。
之后,我又从其他采访工具那里看到了更多的读者留言,那些留言加倍证实了我们事前的一种想象。在线上资料库里搜索“东莞图书馆”,我发现有一组最新揭晓的讨论辑,是各地图书馆行业的专家讨论东莞图书馆留言事宜的。我一个个查了名字,发现都是馆长或者高校图书馆系主任,他们的文章和事例里,有大量对李东来馆长和东莞图书馆的谈论和回忆,这部门内容,加上此前采访里的内容,让我终于获得了一种确定性,就是这个故事,或许只能发生在东莞图书馆。
就像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说的,留言形成新闻热点,看似简朴,实在背后的寄义很厚实:“它呼应了人们对经济衰退、萧条带来的社会生长不确定性的焦虑,对事情、居住地变换或迁徙造成的生涯质量下滑的担忧,对未来物质生涯与精神生涯能否相互杀青平衡的渺茫等。”
我自己以为最主要的一点是,东莞图书馆和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实践,提供了动荡年月最名贵器械——希望。
东莞图书馆一角
开头与末端
初稿我写了两个题目,第一个叫《吴桂春的情书》,第二个是《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情书”“葬花词”“打胶机”,这三个意象都是采访中得来的。在我最先构想第一小节写什么的时刻,它们几个自己出来了。
写开头用了最多的时间,每次写开头都是最难的。最后一次采访吴大叔那天,是周五晚上。第二天不用上班,他可能对照松懈,就喝得有点微醺。我一直想跟他好好聊聊《红楼梦》,第一次采访的时刻,他说能全文背诵葬花词,我也想求证一下。正好那天他自我的大门对照松懈,就趁着醉意给我背诵了全文。我那时就想,要把这里写到开头。
有点好玩的是,那天他喝多了,加上湖北方言,有的时刻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比他跟鹦鹉较量那段,那天晚上他在宿舍给我回忆的时刻,我实在是没听明了的。厥后写稿前看速记才发现,噢,跟鹦鹉较量呢。我绝不犹豫地把这段放前面了,由于他还说了句脏话,“妈的,鹦鹉都能背八句,我是小我私家我还背不下来,我就白读了。”
末端的确定对照简朴,险些是在他们办公室看到那段读者留言,和李东来的那页PPT的时刻,就知道末端要收束在“人的要求”上了。
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珠三角?
最后,谈一谈稿子的第三层,“珠三角性”,或者说,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珠三角吧。
我在珠三角的佛山事情过两年。稿子里有一位采访工具,是东莞图书馆的研究馆员杨河源。杨先生以前在佛山图书馆事情,他和同事从1995年开创了海内首个图书馆公益讲座。他也是一个每到“两会”都市被记者追着跑的那种政协委员,从来不惮于为内陆公共事务发声。加上他正好调到东莞图书馆,我以为他的实践,他对东莞的考察都很有价值,以是采访了他。
我们在松山湖图书馆边走边聊了三个小时。那天除了他本人的事情,我最想获得的是,李东来是一个怎样的人。由于他一最先就通过同事拒绝了我的采访。采访不到本人,下笔总会有不安全感。他作为馆长,已经有15年时间。这个图书馆的运营里,一定有他本人的气质和价值观贯串始终。许多故事最后肯定是不写进稿子里的,但这小我私家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搞清楚。从王艳君那里,我获得了许多详细的形貌。在杨河源这里,我想得到一些更抽象的评价。
包罗“珠三角性”,我也希望杨河源先生从他的角度去做一个考察和谈论。他在这里已经生涯了25年,体会到一种属于南方的“迷人适用主义”。包罗我去采访鞋厂老板,采访图书馆的许多事情人员,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若干很多若干这方面的故事。我因此确定这种总体性的地域空气,不只是我一小我私家的感受,于是就笃定地把它作为稿子的第三层视域来举行叙述。
许多时刻,我们会有一种牢固的见识,就是文化或者社会空气这种器械是抽象的,这种看不见的器械,不具有生产性。它不是高速公路,不是流水线,不是机械大工业,它无法生产实物。但在思索为什么故事会发生在东莞或者珠三角的时刻,我会想起英国著名文学指斥家雷蒙德·威廉斯的一个理论,“文化唯物主义”。这个理论以为,和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物质的二元对立观点相反,文化自己就是一种物质的器械或生产的历程。
我想,若是没有珠三角温暖的物候,不会有“三和大神”群体的泛起。若是没有珠三角的历史文化语境,也许率也不会有纪录片导演周浩的《厚街》《差馆》,不会有诗人郑小琼和许立志的创作,不会有曾经的市场类报业的绚烂,甚至不会有“五条人”。
南方多元,生猛,迷人。在大都市治理机械的开动越来越正确和狂妄时,一个都市,一个区域,有若干弹性的空间和多元的孔隙,可以让人有尊严、有可能性地生计下来,这或许是南方履历里最名贵的部门。
东莞老城区,斜阳下的骑楼和街道
我记得写完稿那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北京SKP事宜。我异常气忿,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对同类可以狂妄到这种境界,而一个都市的气息和运行逻辑,究竟是经由了怎样的渐变、突变或者折叠,才变得云云坚硬和无情。
我因此十分确定,“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的有时背后,一定是一片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土壤的培育。培土人不只是公共图书馆的从业人员,另有媒体行业、NGO事情者、社会事情者、开明的政府事情人员,包容、适用的市民社会——由于他们的通力合作,再加上珠三角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空气,才最终会有这件事的泛起。
但我知道这个器械越来越少了,写出来像一首挽歌。以是转发的时刻我说,这几年地球上漂浮的每一块大陆都在以差别速率淹没和颠倒,所幸一些曾经经常泛起厥后逐渐消逝的公共价值观,像孤岛一样还存在于公共图书馆人的实践中。
一位读者说,“在南下的高铁上读完了《人物》杂志这篇,把自己生生看哭了。心里真是又温暖又忧伤,唤起了我所有关于南方的影象。”这也是我的感受。温暖又忧伤。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谷雨设计-腾讯新闻(ID:guyuproject),原题目《安小庆:若何把已经写滥的选题只管写得“坦荡”》,作者:安小庆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html/2020/0906/31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