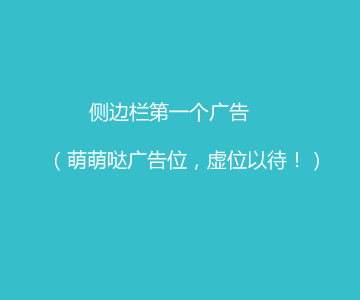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原题目:《文学不应在无人处落难:文学bot有格言化的危险,亦有公共性的难得》,头图泉源:IC photo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玄色的春天。
二月,帕斯捷尔纳克要大放悲声抒写的二月又在人世编写偶然而真实的诗章。只管书籍被燃烧,只管诗人被流放,人类语言的杰作总能为其读者心中未能言说的忧伤与痛苦找到适当的表达。一月、二月、三月和四月,许多读者与各种文学bot一起,在加缪、格拉斯、索尔仁尼琴以及一切有泪与痛的凡人的不朽语言里找到慰藉、灵感与希望。
文学总在私人与民众间进退,它是作家的自言自语,却也是一个生涯在社会里的人面临天下的言说。从降生之时起,文学既是小我私家灵性的思索,也有被看成人类公共交流宝贵财富的潜质。
在信息化时代,当文学bot带着被截取为段落、语句甚至词汇的文学再度踏足公共空间时,我们又一次瞥见文学公与私之间的那道深渊。
一方面,被肢解的文学难免在流传中被“格言化”,热心者忧虑,文本原初厚实的意涵遭受着窄化甚至剥落的危险,而格言自视为真理的狂妄也会减损文学谦逊的品质。另一方面,随着“文学无用论”甚嚣尘上,文学的诋毁者态度愈发轻视,文学的兴趣者也不禁犹疑:
文学是众目之下的痴人自语吗?若是文学不被大多数的民众谛听,若是文学只是流量时代的末流,若是在民众眼前言说的文学最终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治罪,文学是否只应在无人处落难?
一个又一个的质疑险些要将文学的声音压倒,而我们须明了:文学是自我嫌疑和对话的语言,若是在文学性的语言里,我们听见了难以容忍简直凿和狂妄,应当被审阅的,是言说文学的方式;文学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它不屑于以暴力胁迫得来的认同,相反,它力争以提议、交流的方式开拓我们的视野,这种追寻真与善、一致与自力的气质,正是今天文学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必要与价值。
文学“格言化”的危险与狂妄
清明节当天,@俄罗斯文学bot收到了五份内容相同的投稿。“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老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结尾处,阿廖沙在伊柳沙葬礼上的讲话。祭祀想念之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已往的悼念之辞似乎与现实有着玄妙奇异的交相呼应。
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不缺乏流动性,它是有翼飞翔的话语,率领我们在已往、今天与未来间自由地穿行,从遥远之境回溯到身边的一方土地。
好比陀式所言的善良、老实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被视为道德起劲的偏向,再好比鲁迅作品里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在21世纪仍展现出坚韧的活力:当互联网向盼望共情的人们展示破碎、断裂的天下时,援引“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失望之人与百年前的鲁迅履历着相似甚至相同的落寞;当狂人痛斥“吃人”,疾声呐喊“从来如此,便对么”时,怀有常情、识得常理的读者不会感受不到气忿的震颤,于世间一切差别等的榨取中听见声声回响。
在此层面,我们可以说,好的文学有格言的气力,它如迷雾中点亮的灯塔,予人上下求索的动力和希望。一部作品降生的年月和地域或许与我们相距久远,但它的呢喃之语、激切之言常使我们感应亲身之痛,亦或拾起对高尚的瞻仰。
@俄罗斯文学bot在清明节收到的五份投稿
《企鹅版文学术语与文学理论词典》对格言有这样的注释:“它是对真理或教条的简练陈述,是一种精炼的归纳综合。”当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从语境中逃逸,并以自力的面目广为流传时,文学“格言化”了。它是对道德典型、正义诉求的精炼归纳综合,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美妙的理想,纵然在“普世”饱受抨击的时代,这种理想依旧含藏着追寻“真”与“善”的普遍性倾向,其真理色彩也由此愈发浓郁。
剥离文本之后,作家写下的机敏、简练之辞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它们获得了四处游散的自由,也因而陷入了尴尬的田地:它们可以是万物的脚注,却又似无所指一无所有;它们击中了症结,却又无法切入肌理。
作为时评的“格言化”文学语句用凝练的语言和正确的词汇唤起人们的同情、悲痛与愤慨,但它在剖析上的效果却不能让人满足:语境为话语圈定了发生作用的局限,当语境被抽离,话语的有效性在无限延展的空间中变得稀薄。
此外,“格言化”文学的另一个隐忧是,精炼的归纳综合是否会带来容易的满足感,让人们止步不前,发生逃避深层探讨的惰性。近年来,公共舆论讨论问题时对“民族性”/“劣根性”一词的小心正是一例。
“格言化”文学面临的逆境也是各种文学bot无法回避的问题。受限于社交网络平台的新闻公布规则、版权等因素,文学作品不能能以大篇幅、完整的形式出现在文学bot的账号上。
早期,一些推特上的文学bot专注于连载某一本小说,推特文学bot@finnegansreader和@Ulyssesreader通过每条140词的推文连载了《为芬尼根守灵》和《尤利西斯》。不外,此类连载小说的文学bot没有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文学bot主流。现关注度较高的文学bot内容通常由读者投稿的作品选句或选段组成,对文学bot的诟病也由此而生。
脱离文本是否会扭曲作品本意,使之“浅陋化”,是文学bot话题中常见的一个讨论。@亚非文学bot曾发博探讨过文学脱离文本之后的“格言化”问题。运营者以为,或许由于相关靠山知识的缺乏,读者总会“情不自禁”地将文学语句中的时间与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作比较,只管此种类比有一定的缘故原由,但在对比之中,差异性流失了,“亚非”代表的天下款式边缘区域还可能在这样的类比中再次被主流所同质。
@亚非文学bot所表达的忧虑旨在呼吁读者加深对全篇文学作品及其靠山的领会,所针对者,是“格言化”文学所可能带来的惰性。然而,“脱离文本”却面临着从公共探讨滑向指责个体的危险。
@俄罗斯文学bot清明节公布的微博激在谈论区激起了一场争论。一些网友以为投稿内容的高度雷同是“没有个性”的“人云亦云”和“复制粘贴”,部门人甚至质疑投稿者是否阅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从一部艰涩难读的作品中选取投稿素材,是否有“文化炫耀”之嫌。
@法国文学bot的置顶微博
剑桥大学的格言类书籍编辑迈克尔·坦纳以为格言有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品质”。许多格言简直来自各领域的权威者,其中的“模糊、悖论以及智慧元素”无意间将通俗人与真理、真相区离隔,在坦纳看来,格言对人发生威压,“若是你差别意这种说法(格言)的话,你就是个榆木脑壳。”
但值得细思的是,与其说格言的狂妄泉源于文体自身,不如说来自于对格言的言说方式。格言的文体或许导致了它给人惊讶但又有些朴陋不足的缺陷,但当人们使用格言作为终止讨论的手段时,格言的狂妄才变得叫人难以忍受。
在良性的讨论中,格言的使用是对其创作者权威的援引,同时,格言的模糊指向损坏了当下特定问题的界限,使对方无处着力回辩。格言可能是话题的终结者,因而令介入话题讨论的人生厌。
但文学bot中的“格言化”文学语句没有壅闭人们对语句、著作自己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探讨,何来“炫耀”之狂妄?相反,那些被分享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话题的开启者。在微博各大文学bot的谈论区里,不乏有益的文学问题探讨与阅读经验交流,一些@亚非文学bot的读者指出,@亚非文学对阿拉伯天下的关注填补了西欧文学历久占主导地位而导致的不足,纵然这种起劲微末细小,但也胜过一派冷落。
值得玩味和细思的是,“没有个性”“复制粘贴”以一种可谓荒唐的姿态指向了它们自身。这样的指责类似“复读机”一说,以为人只能机械性地重复他者的言辞和看法,不信赖人能从语言的碰撞和头脑的交锋中学习一二。
文学语言的意境难以模拟,更不消说复制,比起对文学语言的分享,被无节制滥用的粗暴辞藻才是语言损失个性的堕落。在被饭圈用语和句式高度挤压的网络空间,文学bot似沙漠上零星涣散的绿洲,作为通俗读者的我们,分享自己喜好的选段,又有什么缺乏“个性”之处呢?
文学bot与文学的公共性
网络流传过程中,文学的多层次内在可能由于“格言化”而层层剥落,更甚者,一些经典作家也许也不会想见,自己作品中的词汇竟能走到截然相反的路径上。文学bot上碎片化的文学选段能在何种水平上助力阅读?文学作品是否更适合私下阅读,而非进入公共社交平台?
这些隐忧呼叫阅读完整性的回归,但犹如有关文学bot的诸多争议一样,它暗含了对文学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嫌疑。
“涵义浅陋化”与“念书炫耀论”都对文学在公共空间内的作用持消极态度——在前者看来,文学能激起厚实文本内在讨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意义被削弱是断章取义及大众流传的宿命;后者则以为,阅读乃隐秘的私事,只可漆黑举行,公之于众不但对社会问题无所助益,照样私人德性的松弛,文学的深刻意义似乎只能于书房的冥想中降生。
加州伯克利大学修辞学教授弗里德里克·M·多兰在《阿伦特论哲学与政治》中谈到,苏格拉底被治罪后,柏拉图便对城邦生涯失望,他深刻地质疑,小我私家的头脑是否真的能影响公共事务。哲学家们最先对公共生涯感应厌倦、恐惧与疏离,多兰称之为“柏拉图的精神创伤”。徐贲在谈论文学的公共性时指出,文学创作者也履历着“柏拉图的精神创伤”。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五四时期的文学还洋溢着社会革新的美妙期许,却在往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逐渐迷恋,许多作家从民众人物退为寂寂无名的失意者,写作也从一种拥抱激情的理想跌落到无奈的且自抒情。
黎巴嫩自力摇滚乐队Mashrou' Leila的MV截图 文字稿件之外,@亚非文学bot还刊发了不少视频内容
“柏拉图的精神创伤”的阴霾不但笼罩着从事精神创作的哲学家与文学家,通俗的读者同样履历着阵痛。“文学无用论”是轻视文学的诋毁者的呐喊,也是许多文学兴趣者心内深种的疑窦。
在@亚非文学bot退圈事宜中,有人讽刺说,亚非文学bot一年的谋划还抵不上明星在短短几日里带来的流量。继“柏拉图精神创伤”的政治无能后,文学又被流量裁定为经济无用。
一些看法以为,文学bot是少数文学兴趣者的“圈地自萌”,与数目上占多数的“民众”无关,因而不具备普遍的公共性。
徐贲在《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一文里破除了这种对“民众”数目化、单一化的明白。他指出,“民众”常被明白为“大写的、单数的”Public,但在“自由的公共性”中,“民众”是面目多样的、详细的复数(publics),每一个“小民众”都有自己的兴趣、审美以及价值取向,“小民众”之间是可交流相同的。
社会当中有民众对文学感兴趣,自然也有民众对文学无感。纵然文学bot的受众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多数派,文学也欠妥被驱赶回书斋。良性的公共空间为“小民众”的合理的自我表达与出现提供空间。当这种良性公共空间坍缩时,我们在矛盾与冲突中无法再看到基于尊重和一致的对话,暴力的攻讦取而代之,“小民众”的共存变成了排除异己的驱逐竞赛。
相反,自力的文学,其作用总是“有限的”,它以自身魅力吸引潜在的受众,而非通过指使、怂恿与威胁索取强制性的、大规模的认同。
因而在文学的作用与公共性饱受质疑与创伤的今天,文学能在公共社交平台有一席之地是难得的。文学bot的形式可能会带来“格言化”的弊病,但文学厚实了网络天下里的“小民众”,提供了一种与流量相悖的思索方式——况且,正如一些谈论者所说,文学bot并不会使文学失去其原本的读者。
在文学进入公共空间后,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文学能在多大水平上促成“自由的公共性”。这一问题现在还无法获得很好的回覆,既有人认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信赖阅读文学能培育人对主体性和自我的熟悉,也有人像文学指斥家乔治·斯坦纳那样指出,一小我私家可以在夜里读歌德和里尔克,日间到集中营去上班。文学的某些特质中藏有“自由公共性”的因子,但阅读文学与“自由公共性”的培育之间或许缺乏一定的联系。
同样,文学bot的存在未必能促成网络空间的“自由公共性”,但于文学bot公布的内容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文学品质的辉煌,它至少起劲涉足我们惯常视野之外的天地,开拓了一些公关议题,或是呼吁了新的视角。
例如,@亚非文学bot曾刊发过一条来稿,内容是伊朗裔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Hamid Dabashi对伊朗裔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著作《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指斥。
Dabashi以为,纳菲西的书是“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前沿的权威著作”,书中对伊朗历史靠山的“显著忽视和彻底洗白”是美国全球霸权下团体遗忘的表症,作者滥用合理的女性一致诉求来表达美国霸权的不合理目的,将伊朗描绘成相符西欧人的漆黑“东方理想”。对Dabashi而言,此书最大的问题在于诋毁了“所有竞争性的非白人文化”。
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描绘了伊朗政府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并纪录下自己与学生用文学阅读作为抗争手段的隐秘作乱。2011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文版问世,在豆瓣念书上获得8.5分好评,但中文天下里,指斥或是相异的声音却很少。
@亚非文学bot曾在“来稿须知”中说明,“在西方国家影响力大于在亚非国家的文学”概不接纳,因而,在这里我们不会看到《追鹞子的人》《我在伊朗长大》等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中东文学著作。
@亚非文学bot为主流出书读物之外的文学提供了一个被瞥见的机遇,对边缘者“异见”的接纳,让我们得以反思:我们此前被放置在怎样的位置上去旁观天下?
“若你感应绝望,记着此间的洪流” @亚非文学bot公布的伊斯坦布尔陌头妇女游行口号
除此之外,@亚非文学bot厚实的内容形式和对“文学”的宽泛界说中蕴藏了文学公共性的新启示。与其他文学bot差别,@亚非文学bot在稿件的接纳上更为天真,除传统文学文体外,漫画、歌曲、影戏台词、口述纪实等,凡“承载意义”的文字均可作为文学来稿。
徐贲将阿伦特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叙述总结为“说故事”,文学对公共事务的经受即在于说出人类社会所履历的一切,辅助我们学会面临和接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又或许是将要发生之事。
年头伊朗导弹击落客机后,@亚非文学bot刊出了一篇伊朗阿米尔卡比尔大学学生的文章,作者写道:
作为伊朗的后代们,我们从不把自己和祖国人民分脱离。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们心底的悲痛在我们的胸膛中承担着一致重量。悲剧在星期三早晨到达岑岭,在几十名公民死于克尔曼的踩踏事宜中后仅一天,伊朗再一次眼见她的子民落入地平线。我们还没来得及为八月的殉道者的殒命感伤,就要面临新的悼念。
这段庄重悲肃的文字在Telegram群组上广为流传,急就的文章或许无法跨入文学经典的殿堂,而文学的生命依旧在遭遇魔难的肉体中跳动,在远方的心灵间流淌。
尾声:文学bot要保持所谓中立吗?
哈贝马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最初是在文学阅读中形成的。人们在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场所讨论文学,培育了公然言说与批判的意识。
文学bot虽然没有直接揭晓对文学或时势的一手意见,但正如上文所说的,“格言化”的文学语段为其读者提供了久被遮蔽的视角和弥补性的关注,格言模糊、艰涩的特质还会让一些人在习惯性快速滑动屏幕时停下来思索一二。文学bot不是在单纯地做名著转动播报,或是用名人名言赚取流量,它对公共空间的建设需要被发现和一定。
文学bot介入到公共讨论之中,已经引发了前文提到的“格言化”“念书炫耀论”等一系列争议,而文学bot也因bot的身份屡遭质疑。
一些人以为,文学bot既然以“robot”为名,当去掉运营者的主观态度,务求中立。实际上,文学bot自降生以来就分为两类。一是真人运营的账号,一是由编写好的程序代管。且岂论程序中是否夹杂着编写职员的小我私家取向,倘若要求真人运用的文学bot保持中立,“中立”又当做到哪种水平?
若是以bot名称为限,“俄罗斯”“亚非”“法国”应当限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局限,照样有更庞大的考量?
@亚非文学bot接纳的即是后一种计谋,将受奥斯曼统治与泛伊斯兰文学影响的欧洲巴尔干半岛纳入接纳局限,不接受市场主流亚非文学投稿的规则也确实为更多尚待挖掘的文学撑起了更多空间。若是要求运营者做到“来者不拒”的中立,那么@亚非文学bot在公共议题上的拓展和文学领域的挖掘就只是空谈。
在文学中追求中立是危险的,它将导向没有态度的漠不关心,就像深夜阅读歌德和里尔克的纳粹。斯坦纳在《语言与缄默》中忠告,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圈套,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把文学教成似乎是文质彬彬的职业,是例行公事,这比教欠好还要糟糕。”若是阅读不能凿碎我们心里的冰海,文学不外是暴力最下游的托辞与卖弄。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html/2021/0907/4865.html
- 上一篇:华宇登录下载地址_方舱医院的宿世今生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