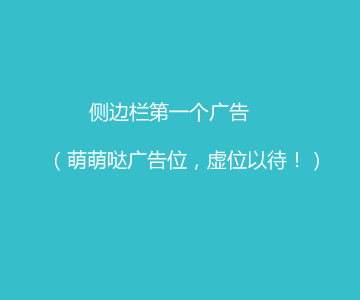虎嗅注:本文首发于2018年,若是你是个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或许已经看过戴锦华先生这篇采访。她提出了诸多看法,都在印合我们的社会走向,大女主、小鲜肉、耽美改编……这两年的影视文化照样那回事。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组织精细化的天下,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团体,却又不得不在社交网络上相聚。性别议题声量这么大,但我们捕捉到了什么转变?
题图来自日本影戏《跨越栅栏》,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作育(ID:xingshu100),原题目《女性的自由,仅仅是“花木兰”和“白流苏”之间的选择?》,采访:吴海云、李莹,文字:漫倩,校对:其奇
重新手艺革命的袭击到文化工业的女性主体性凸显,从女性的“被旁观”、“被凝望”到女性自动“旁观”,女性是否在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主体位置?
当J.K.罗琳、安妮·赖斯等女性作者缔造的文本风靡全球时,当日本、韩国,甚至中国盛行文化中女性向的女性誊写、粉丝经济成为了文化工业中强有力的部门,女性介入今日的文化生产,甚至引领和主导文化生产时,这会是再一次的消费主义式的落网,照样一次女性的新机遇?
“把女性问题,当做一个社会提高的一个标尺,会犯错的。”
“我真的经常以为两个个体之间的差异,远大于性别差异。”
“人类的一半是女性,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刻,我们一定是整体地在以某种方式去触碰今日天下,去触碰今天整个天下的结构、文化、规范,整个天下的主流与支流。”
——戴锦华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影戏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作育:您以为“小鲜肉”为什么会成为当下的娱乐潮水?
戴锦华:我以为首先所谓的“小鲜肉”(的盛行),实在是跟包罗好莱坞在内的全球影戏工业中的明星、演员,偶像的岁数普遍降低(有关的),就是越来越青春化。
谁人青春的观点,从约瑟夫·康拉德的20岁到30岁(编注:约瑟夫·康拉德,英国作家,1857年12月3日生于波兰,曾航行于天下各地,善于写海洋冒险小说,小说《青春》即为作者凭据本人1883年以二副身份加入一艘开往曼谷港的商船的航行履历撰写而成),到现在变成了13岁到17岁这样的一个观点局限,实在这是两个完全差别的时代对青春的界说,对吧?
“青春期”(这个词)的发现是二十世纪六十年月,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功勋(编注:二十世纪六十年月,美国肯尼迪政府缔造并推广了“青春期”、“代沟”等观点,对那时的民权运动起到了助推作用),青春的观点在谁人时刻就完全被改写了,不是青春年华,不是青春岁月,不是青春阴影线,而变成了青春是化冻的沼泽,青春是躁动,青春是生长的烦恼,青春是作乱,甚至疯狂……这是一个大的文化上的因素。
而另外一个大的因素呢,是全球盛行文化工业的走向。
今天这种青春偶像,实在是日本文化逆袭的效果,对吧?从日本动漫——若是你一定要追溯的话——还包罗了日本人关于樱花,关于青春,关于生命,美,爱和殒命之间的那种,不好意思,我要说很病态的纠结——这样的一种器械返销西欧,经由西欧影响到全天下,造成了青春偶像越来越年轻化的征象。
年轻就意味着某一种美,某一种可观赏性,通常它不只指男性偶像,也指女性偶像。好比说,上一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戏,这是第一次饰演者自己的年数和莎士比亚的剧情中一致,以前都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来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编注:在莎士比亚原著中,罗密欧17岁,朱丽叶13岁),或者好比说2011版的《简·爱》,也是演员真实岁数与剧中人的岁数相仿,这是一个方面的主要转变。
而另一个方面的转变,才是跟所谓的腐文化相关,就是说男性的青春化。这种青春化是以性征不鲜明为特点的一种“中性”的、稚嫩的、娇嫩的美。我以为这实在只是这类文化当中异常小的一部门,而不是它的所有。
而我自己会说这内里另有一个层面,就是全球劳动力结构的改变。
这个说起来比较庞大,与劳动力市场向第三天下外移有关。现在这些所谓的蓬勃国家,包罗中国今天的大都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先改变。
换句话说,弃民的人数在增添,劳动力结构上不被需要的人口在增添。这造成了劳动力岁数结构总体的下降(编注:弃民,结构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动力,资源主义经济学、统计学意义上的多余人)。
以是当下我们的青春崇敬中,还包罗了某种(对朽迈和被镌汰的)恐惧,由于(迭代转变)太快了,太早地我们就“老”了。
以是我以为像适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一样,这(“小鲜肉”的盛行)是一个异常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转变,而不单纯是一个女性男性的问题。
作育:若何解读小鲜肉的“娘化”引起的争议?
戴锦华:攻击这种文化和消费这种文化的人,通常不是同一群人。
在今天这个分众的文化市场中,他们的阶级结构、生计方式、文化态度可能完全差别,攻击者自己可能是道德守旧主义者。他们之间可能有差别的文化意见意义,对文化有差别的想象。以是我以为很难把他们真的放在一起来讨论。
2016年,鹿晗在微博晒出一张自己和上海陌头一个邮筒的合照,引发大量粉丝深夜排队和邮筒合照,队伍一度长达300米
至于说所谓的“娘炮”,最早我们有一个更熟悉的说法,叫“娘娘腔”嘛,广义上,人们经常把阳刚气质不那么显著的男性称为“娘娘腔”,我以为这是一种对男性的榨取,就是男性不能表现出柔软、细腻、感伤的一面,男子不能流泪等等等等。
此外,“娘炮”这个词里还包罗了对气质阴柔的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实在它和“小鲜肉”彼此之间并不叠加。
然后,我又以为——我真的会把问题庞大化——我以为,这个问题自己没有那么简朴和清晰。不是一个单纯的提高/倒退,解放/压制的问题,而是有更庞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在内里:
一边是“同志不能黑”(编注:此处特指对同性恋、同志运动局限于“政治准确”层面上的认同),可是另一边——许多网剧的编剧跟我讲——网剧一度有两种定型化的角色是必须存在的——以邪恶反常的形象泛起的“剩女”角色和以可爱、穿针引线的形象泛起的“娘炮”角色。这样的设置几乎是硬性划定,若是不这样,他们的剧本就不会被接纳。
然则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实在对于人们对小鲜肉的攻击有所认同。
我的认同是在于,我以为这样一种所谓“颜即正义”、“萌即真理”的文化征象的盛行,似乎是一种进一步令社会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诉求,由于它甚至抽空了内容——粉丝对偶像,所谓的“爱豆(idol)”们的要求,仅仅是他的在场,仅仅是他的一张脸,似乎那就足够了?
作育:小鲜肉消费文化崛起,是否代表着现代女性职位的上升?
戴锦华:也许不是这样的条理。
毫无疑问,它象征着女性在新的数码时代文化结构中位置的上升,然则我要质疑的不是上升不上升,我要质疑的是“女性”。
这是什么女性?这是哪些女性?
由于我以为把性别上的观点和社会群体上的观点混为一谈,这自己就是谣言。
简朴来说,这里的“女性”指的是有消费能力的女性,那么没有消费能力的女性根-本-就-不-存-在。
我老喜欢引用那句话,就是我翻译的副司令马科斯的谁人说法,他说:
“今天的天下地图是经济疆土,不买不卖的人就从地图上掉下去了。”(编注:2006年,戴锦华主持翻译了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运动——萨帕塔运动的首脑“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文集《蒙面骑士》,“副司令马科斯”是个重叠身份极多的人,他用一个假名坦率否决全球化、资源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格瓦拉第二”之称)
副司令马科斯
就是“弃民”,这些人完全不能见。
由于我们今天的领头科学是统计学嘛,你在统计学的意义上不存在,你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不存在。
以是这里我们说的女性,是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女性,也可能你有消费能力,然则好比说,在岁数上,你被流放在获知结构之外,那么你同样不存在。
以是,这内里的歧视可能是阶级的,可能是地域的,可能是岁数的……然后我们(抛开这些)来谈女性的消费能力若何,女性的主体位置若何,女性的欲望若何……我以为就很成问题,很有谣言效果。
作育:女性消费力能够改变女性现状,让她们由此获得权力吗?
戴锦华:是可以让她获得某种“权力”的,然则现在所有的权力,都是资源的权力、金融的权力,通过消费所实现的这样一种权力。
今天是Customer is always right的时代,对吧?“主顾是天主”,“主顾是万能的”。
那么,有一个消费群体就会有一种消费供应,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产物。它是在这样的一个供需关系的资源结构当中存在的,以是市场要不断地开发,不断地细分,市场要被穷尽。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女性群体,况且是接受过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头脑洗礼,都会当中女性普遍就业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群体一定会受到市场的重视。
作育:类似《延禧攻略》这样的宫斗戏、大女主戏的盛行,能反映当下女性职位的上升吗?
戴锦华:这类作品我看得不够多,以是我可能不大有谈话权。然则凭据我看过的相关相邻的作品来说,我的总体考察是,由于资源结构、劳动力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互联网、VR(虚拟现实)等手艺的生长,这一切器械使得性别差异自己,不是那么主要了。
详细到中国的现实,有一些年轻学者的看法我也很认同,就是连续了两代人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性别区隔。直观地说,就是通常的“望子成龙”(的期望)也会投射到女性身上。他甚至是“望女成龙”,不是“望女成凤”。这样的一种竞争结构,这样一种对卓越和乐成的追求,同样成为一种压制女性的存在。
是社会整体的转变造成了我们说的这种男性作为欲望旁观工具、腐文化、耽美、大女主等等征象的盛行。在我看来它们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以是我不喜欢单纯讨论女性形象。
若是人人在女性形象意义上,问我对某一个大女主的看法,我就只能支持,对吧?由于这是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一个壮大的女性形象,区别于传统的、邪恶的或者柔弱的女性形象。
然则并没有这么简朴。
《延禧攻略》中饰演女主角魏璎珞的吴谨言
我对这些(大女主)作品心情庞大的地方,在于它们通常只是更换了角色的性别身份,然则丝毫没有改变故事的权力逻辑。
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她仍然是广义的文化上的“花木兰式境遇”,就是你要登场,你就只能化装成一个男子。这里固然不是指外在的化妆,而是内在逻辑的置换,就是女性不再代表着另外一种逻辑,或者是逻辑之外的逻辑。
我一直很少单独谈性别议题,然则一直坚持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缘故原由就在于我一直寄希望于女性的生命履历所累积的历史能成为另外一种资源,一种完全差别的面临由男性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资源,以便给我们打开可能性。
若是不是,若是不能,若是说女性只是男性的另一个版本,而且是在逻辑上没有差异的版本,我就会以为它不是那么新鲜,或者那么有价值。
同样的期待,也可以放在所谓耽美(编注:“耽美”一词出自日语,本义为“唯美、浪漫”,作为一种派系而言,耽美派曾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盛行于20世纪30、40年月,60年月以后,这个词逐渐从原意中脱离,变成了漫画中一类派生产物的统称,现在一样平常用来表述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恋爱)作品中,主要的不在于女性去想象男性之间的欲望。
我曾经期待这样的故事当中,同时通报差别的情绪逻辑、行为逻辑和社会逻辑,但令我失望的是,我在其中看到的是同样赤裸的权力逻辑。
我想提醒人人,想象不必那么单一,想象原本应该有更多的路径,而且应该打开更多的空间。
作育:相对来说,您更倾向耽美文化对社会带来的差别价值?
戴锦华:在我和所谓的腐女和所谓耽美的作者大神们的交流以及进一步的阅读当中,我以为它同时还包罗许多其它层面。
好比说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耽美虽然也被包罗在广义的言情中,然则它比言情更稀奇的地方在于,它在实验为社会提供一种修复性气力。
这个修复性的气力就是,若何毗邻起小我私家与小我私家,若何在小我私家与小我私家的毗邻之中,重新建立起一种与社会的毗邻或者是对社会的负担。我以为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种亚文化,这样的一种文本,它在实验去负担、去直面今天我们这个网络时代宅男宅女们所面临的“小我私家主义绝境”。
我使用“小我私家主义绝境”这样一个词。我以为“宅”、“宅生计”真的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小我私家自由,它甚至让我们制止了许多人与人之间似乎无法制止的宿命式的悲剧境况。
然则,自由的宅人们又亘古未有地被约束在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之中,简朴地说,就是全球的物流系统、电商系统、金融资源。与这种自由相伴的,是岌岌可危的平安……像吊在树上的一个个小小的蜂巢。另外一方面呢,绝对的小我私家主义生计自己,并没有改变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和组织化的事实。以是我把它称之为“小我私家主义绝境”。
耽美文化艰难地试图去建立起亲密关系,进而由此来恢复社会性,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以为就很有趣,很有趣。
作育: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提出“雄性衰落”一词,指出现代男性正在衰落,男性面临危急,您若何看待?
戴锦华:我以为这种说法形貌了一种事实,然则呢,也可能遮蔽了一种事实。
由于我以为可能主要的不在于“雄性衰落”(编注:雄性衰落,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提出的看法,以为“雄性正在衰落,男孩面临危急”。在高科技飞速生长的环境靠山下,学业成绩下降、社交技术匮乏、药物滥用、着迷游戏和色情片等征象在男孩身上习以为常),在于我说的新的生产结构、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
曾经我们说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我以为现在是:在网上,没有人在乎你是男子照样女人。
不是说网络没有性别文化,实在网络有更赤裸、更直接的性别歧视文化,然则在网络上,你是男子照样女人,仅仅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标注,没有人会深究你事实是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性别饰演就变为了一种基本事实,当你标注的时刻,意味着一个自我设定的人设,一个关于你自己的人设。我以为这是一个缘故原由。
然后另外一个缘故原由就是当非物质生产成为蓬勃国家和地区的主导性生产的时刻,传统劳动分工所支持的那种阳刚气质,就不再是一个充实必须的器械。
然则我又说它没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我们这么说的时刻,把视野放在了蓬勃国家、蓬勃地区、大都会。可是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人类的生计照样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照样“没有农民,谁能活天地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那些在大田里耕作,在流水线上生产,在矿山内里做奴工的人来说,劳动分工和榨取结构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分工完全没有改变,也不能能改变。
戴锦华教授在采访现场
以是,每当人人说“天下上”的时刻,我就真的,每一次都许多余很矫情地问:
哪个天下?哪种女性?哪种男性?
真的应该问。
作育:您以为当下女性应该忽略性别局限,去追求自我实现吗?
戴锦华:在我生长到朽迈的历程当中,我确实考察到这种内在的改变。
我们喜欢说50到70年月男女都一样的制度对女性构成了另外一个意义的危险和榨取,对吧?由于那时的女性被结构性地划定要和男子一样,或者说花木兰嘛,就是我们要化装成男性,然后遵从男性的逻辑,像男性一样地去争取自己的社会成就。
我以为今天我们再回过头看,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样一种结构和制度性的划定,在社会意义上,给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种硬性环境。
我看到在整个中国社会再次最先发生转变,性别的差异、女性的权力最先被重提的时刻,实在它同时打开了一个退却的空间,打开了一个自我原谅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不以为今天我们有了所有家用电器的辅助,有了家庭服务、家庭劳工之后,今天的女性还比昔时“双肩挑”的母亲们更辛劳,或者更艰难。
我曾经和影戏学院的导演系系主任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们78班(编注:指1978级)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厥后你们(系)突然变得连五分之一都不到,甚至最后几乎没有女性了,(为什么)?”
这位主任是男的,他说:“真的不是我之所愿,是由于没有女生报考,以是导演系的女生才会变得异常异常少。我总不能为了性别比例而录取不够格的学生吧?”
厥后,我问到一些影戏的女性从业人员,她们就说:“导演这活不是女人干的,太累!”
那么若是我们回去,去想昔时的黄蜀芹导演(编注:中国女导演,1964年结业于北京影戏学院导演系,代表作《青春万岁》、《童年的同伙》、《人鬼情》、《我也有爸爸》等,作品曾获包罗柏林影戏节在内的多项国内外大奖),她们那一代人,她们也许不是由于累而选择它或者拒绝它,以是我以为总体的结构转变,照样有影响的。
然则我也赞成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性别的定型化想象和性别歧视最先被结构珍爱,甚至最先被制度支持。这种制度纷歧定是社会制度,也可能是公司制度。
我自己履历过1995年天下妇女大会(编注:第四次联合国天下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来自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15000多人出席了集会,是迄今参加人数最多的联合国集会,也是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集会),那是一个异常有趣的年份,异常有趣,那一年中国各大事情市场(包罗妇联)的主要岗位,往往都在招聘需求里明确地标明性别为“男”。它解释整个的制度性转变的发生。
以是我就一直说,讨论性别问题,一定不要用那种线性的向量结构去权衡提高照样倒退。有时刻在社会总体提高的时刻,性别议题在倒退,有时刻在性别议题异常前卫的时刻,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异常胶着,甚至倒退的状态。
把女性问题,当做一个社会提高的一个标尺,会犯错的。
作育:为什么说女性问题成为权衡社会提高标准是会犯错的?
戴锦华:你以为性别状态异常好的地方,社会就是在提高吗?人整体就是处于解放状态吗?然后当性别议题最先恶化的时刻,社会就整体地在恶化吗?
有相关性,但并不永远正相关。
简朴地说吧,八九十年月,中国社会最先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整体地处于提高状态——若是我们把小我私家权力,把物质生活,把经济生长都作为尺度的话,毫无疑问,中国社会那时刻是处在一个提高的状态之中。然则整个八十年月,我经常直接简朴地用四个字来形容——反攻倒算。它是一个男性群体整体地对女性群体“反攻倒算”的年月。
作育:您不就是八十年月出来的吗?
戴锦华:你以为我(成为今天的我)就证明了八十年月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年月吗?
我是之前的谁人年月所作育的。你要看八十年月生长的人,厥后他们的状态是什么,他们的性别意识是什么,他们的性别生计状态是什么。
从八十年月到九十年月,整个中国社会的性别整体状态是在履历一个连续的,要我说的话,恶化的历程,而整个中国社会是在一个提高的历程。
但你真的做细分的话,对于女性个体来说,她可能同样分享着这个提高。由于这时刻,她有权力选择做家庭主妇照样职业妇女,她自由了,她真的自由了。
可是我也许整个地履历过谁人时期,许多选择去做全职太太的女性,厥后走向了两种大的趋势:一个是在幸福的无聊之后,重新回到职场,而另外一种很悲凉,她们最终照样没有逃走最古老的女性运气——成为被遗弃者。
由于谁人时刻,当她们使用这个自由、享有这个自由的时刻,不知道所有的自由都是有价值的。
周润发及缪骞人主演的影戏《倾城之恋》剧照
做一个职业妇女,支出的价值是我履历过的,我的母亲一代履历过的,我的孩子们也在履历着的;然则,做一个好比《倾城之恋》之中的白流苏,要支出什么价值,那是白流苏们才知道的。
作育:现代女性生长是否泛起了第三种逻辑的苗头?
戴锦华:我给你的回覆,也许不是振奋人心的。
不是说我完全没有看到,只是到今天为止,女性的那种别样的气力,所谓alternative,女性的这种纷歧样的气力,这种由她们自己的生命履历,甚至身体履历中发生的资源,经常只是在社会处于绝对的危急或者陷入无助状态当中才能够获得施展。
我们的民选村官制度在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后,我自己做过许多的实地考察,我对这个谈话负责任,你就看到,只要这个地方另有一点可分配的资源存在,(当选的)都会是男村长,在那种完全没有资源,村官只能是一个绝对服务性的、牺牲性的岗位,同时要完全用情绪去维护邻里社群关系的地方,就是女村长(当选)。
在天下局限之内,你会看到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陷于危急的时刻,女总统就泛起了,女总理就当选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英国第49任宰衡,也是英国首位女宰衡,有“铁娘子”之称
以是我以为很有意思的就是,人们只有在主流逻辑陷于极端危急的时刻,他们才会选择女性角色,同时寄希望于她们谁人纷歧样的资源和气力。
那种正面的、整个社会都认知到的、女性群体自觉的,这样的(一种自力的逻辑)我还没有看到。
以是我就会很矛盾,由于我并不希望危急整体发作,以便女性自告奋勇来拯救危亡,我丝毫不希望。然则另外一边,我看到当下的主导逻辑,也就是所谓的男性逻辑,它正在把我们往危急的道上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
作育:您若何界说女性主义?
戴锦华:对于我来说,女性主义就是乌托邦,它最真切的意义就是解放。
我以为女性的彻底的解放,一定是人的解放,同时是男性的解放。
我所说的乌托邦是修建在一个很小我私家主义的条件之下,我以为就是尊重差异。
从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仅仅是差异而不是优劣——最先,到更进一步,是尊重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
我真的经常以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远大于性别差异。
作育:现代女性还能选择真实吗?
戴锦华:若是说真实的选择,或者选择真实的话,我以为那后面有个很大的哲学问题,就是熟悉你自己。
由于回覆这个问题,经常要用一生的时间,当我们有了谜底的时刻,经常太晚了。
就是,我到底要什么?我们经常是被社会表示,经常是别人来告诉我们我应该要什么。
我最早听到“宁愿坐在宝马后面哭,不坐在自行车上面笑”的时刻,我那时真的有一个异常质朴的痛心。
幸福和微笑,永远是人生的最终追求,然而你居然以此为价值,去换取诸如财富这样的器械?
然则对于我来说,更大的袭击,不是来自这个新闻,来自我一个年轻同事的回应。当我饭后茶余发这个议论的时刻,她给我的回应是:
“坐在自行车后面,你笑的出来吗?”
这个话真的让我以为痛了,让我以为痛了,我以为这才是至痛的洗脑。
你坐在爱人的自行车后面,纵然面临狂风,纵然面临沙尘暴,你就笑不出来吗?
苍井优和小田切让主演的影戏《跨越栅栏》,讲述了失意男女相互扶持的恋爱故事
横竖我是这样笑着渡过我的青春和恋爱的,我知道那是何等甜蜜。
然则到了你都不能体验这种幸福,你都笑不出来的时刻,那才是恐怖。
以是我就说,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什么是真实?
我们有没有愿望和能力去熟悉真实?我们有没有愿望和能力去负担真实?
有一个稀奇质朴的词,叫求仁得仁。
当你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时刻,你要接受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对吧?可是你坐在宝马后面哭的时刻,你可能要接受的是张爱玲所谓的批发式的性事情者的运气(编注:据称张爱玲说过“女人为了生计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真实性及出处暂无法确认)。
你想好了吗?你选好了吗?
这还只是单纯的在两性、婚姻和家庭的层面上的选择。
而今天,我以为可能更大的问题,还在于选择太多,以致人们无从选择。
以是,在我们还能够选择的时刻选吧。
在你还年轻的时刻选,在你另有机遇犯错的时刻选。
我,纵然在这个岁数,若是有需要,我也照样会选的。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作育(ID:xingshu100),采访:吴海云、李莹,文字:漫倩,校对:其奇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0626/2263.html
- 上一篇:华宇娱乐软件下载_前浪黄光裕,后浪黄峥
- 下一篇:华宇测速测速_为端午忙碌的湖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