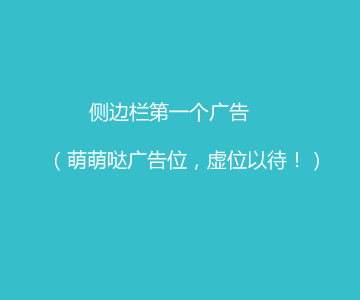同伙圈里有好些人许过要去一趟冰岛的心愿,一年又一年,然则他们从未出发。在想象中,那是一个冰寒的、孤绝的地方。远方的人似乎总要为了寻找些什么才会踏上那块土地。极光,或者某一个问题的谜底。
山月入海在2019年的时刻以交流生的身份在冰岛栖身了近半年时间。刚到那里时,天天要到晚上快11点时才天黑。天气好的时刻,便去海边散步,天气欠好时,就去超市囤够了咖啡和零食,和室友窝在客厅看影戏。在她的笔下,冰岛有关的回忆是清淡、悠远又镇静的。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山月入海,题图:原文供图
一
我在冰岛租的屋子从每个月初最先算,因此,2019年8月下旬,我刚到冰岛时有两周住在Airbnb找的暂且住所。三室一厅,刚满80岁的房东奶奶Birna住一间,我和同伙小朱住一间,另有一间用于聚积杂物。
Birna的屋子很挤。挤的缘故原由包罗但不限于,从天花板到墙面随处可见的工艺品,木雕,绿植,几大摞CD,数不清的唱片、画册、书籍、靠枕,多到可供几十人同时用餐的陶瓷餐具,新鲜的香料,以及铺满地面的印花羊毛地毯。
我是不喜欢穿鞋的人,因此在Birna家里光脚踩来踩去,格外愉快。
8月末天黑的很晚,我房间的窗口朝着海,也朝着夕阳的偏向。天天洗完澡,头发吹到半干,十点多看着太阳落到海平面下方。到了十一点,整个天下都很蓝。Blue Hour和夜晚的敏感相互作用,堆叠出一天中最懦弱的部门。纤细、敏感、无处可逃的情绪。
二
在冰岛打伞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一把天堂伞远渡重洋追随我来到这个与欧洲大陆阻隔的小岛,又险些原封不动地陪我回去。
这里没有人打伞——来到冰岛不久后我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人人都有防风防雨的外衣,一到下雨天,尺度的姿势是戴着帽子半低着头,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不是伞欠好用,只是风着实太大了,而冰岛不起风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久而久之反倒以为利便。不用忧郁忘带伞,还可以在雨天解放双手。
北方的雨水从高悬的天上落下,不轻不重地跌落在手掌心,然后粉碎成更小的水滴,放大了掌心的纹路。
那一瞬间是欣喜的。乌云在赠予,而我在承接。
更多的时刻,雨天意味着一整天窝在家里。花园里有一个封闭式雨棚,我和室友常在那里看书。当暴雨落在铁皮顶棚上时,噼里啪啦的声响让面临面的谈话也难以听清,我们索性放弃相同,一个人蜷在沙发里念书,一个人坐在书桌旁写字,就这样,一下昼。
三
"清闲感"也是让人爱冰岛的缘故原由。这意味着"栖身在这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情绪资源消耗。
之前在加州时,邮箱里堆满了警局发来的平安警报。抢劫、骚扰是常态,枪击也在学校周围的公园里上演。后街的麦当劳住满了homeless不可以去;校园的某几个角落被学长学姐画出红圈,告诉我们十一点以后这里容易被抢劫;学校的校车通宵运行,后半夜甚至可以直接door to door送学生回家。
那时我永远感应不安,即使是日间走在路上,平均50米遇到的两个homeless也让我心惊肉跳。或许是有些太过重要了,但恐惧时时埋在心底,不停地消耗着看不见的能量,让人身心疲劳。
以至于厥后在冰岛,偶然遇到拿着酒瓶子喝的醉醺醺的大叔,也会暗自重要加快脚步。
只管事实是,冰岛在大多数时刻镇静得让人十分放心。在人均1.5辆车的冰岛,马路上的车不少,遇到上下班高峰期也堵车,可人行道总是空荡荡的。只靠步行和公共交通的我常以为有些伶仃。
伶仃,却很自在。可以自言自语,可以高声哼歌,可以随时停下来拍路边的景致,不用忧郁盖住行路的人。晚上十一点突然想吃水果,直接裹上外衣和围巾出门去24小时超市,除了结冰的路面容易滑倒,没有需要避开的地方。
这里对独来独往者十分友好。不需要在夜晚呼朋引伴地回家,也不忧郁一个人住会有危险。
这种"清闲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不必要的忧郁,而节约下来的这些情绪资源可以用来让其他事情做得更好。早起、坚持运动、专心研究一份菜谱、为同伙的生日准备贺卡和礼物,在启动这些事之前,都需要贮备一定的情绪资源。资源在平安感方面消耗掉,自然在应对其他方面时感应力有未逮,之前在美国时我常感应没由来的焦躁感也就不难注释。
四
我以前经常失眠,若是五六点还醒着,多半是在床上苦熬了一夜。在冰岛时也不破例。十一月最先,日照逐渐缩短,十一点才天亮,下昼三点就最先变黑,到五点已经像深夜了。一次晚饭后,直接回房间躺在床上,看着窗外一片漆黑的样子,以为就这样睡了也没有一点违和感,作息完全乱掉。
我有一面大落地窗,面向着夕阳的偏向。日落的时刻,橙黄色的光通过窗子大量地涌进来,将我整个包裹住,树叶间隙的投影也落在每一寸墙面。有风时,整个房间的光都流动起来,像一片光海,而我是在温暖海水里溺水的人,闭着眼下坠。
这时,我会感受自己的是真正被爱、被接纳的,因而所有懦弱的情绪都可以平安地释放,让它们温柔地在我的脑海里游走。同时感应自然与我亘古未有的亲近和它无限包容的精神,感应一种无尽的精神能量,像潮汐一样涌动着。
想起,有好几次,我在冰岛追夕阳,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当我从超市或影戏院里出来时,看到夕阳处的海平面上爆发出浓郁的颜色,经常是橙红,偶然是玫瑰色。那时我总有强烈的感动,想要奔跑穿过街道和海洋,追去海终点处光消逝的地方。可我没有跨越海洋的能力,也跑不外太阳落下的速率,只好看着一整片天空烈烈燃烧着。
燃烧总是优美的,由于它意味着消逝,意味着所有美都肯定在这一回里迸发,甚至带着争先恐后的意味。而火焰则是消逝的预兆。地终点的金黄色刺痛我的眼睛,提醒我这是一团在宇宙中兀自燃烧的火焰,是走向消逝的意思。
因此我总是在这样的光耀落幕时感应悲恸,似乎这是一场纪念太阳消逝的古老仪式,在已往的45亿年里日日上演着,并且在我细小的生命尺度里,会一直不停地演出下去。
这样美得虚幻的天,总让我感应惶惑与不安。这是感性打败理性的效果,我无力抗争,唯有虔诚地守候。等上一整晚,才知道昨天不是散场时,只是一幕落下,待另一幕又起。
轮回着,也消逝着。
五
距离雷克雅未克不远处的小岛上有一束光,一束直冲向四千米高空的光。
小野洋子为了纪念约翰列侬,在Videy岛上确立“Imagine Peace Tower”,每年10月9日列侬的生日亮起。那天晚上,免费的轮渡把雷克雅未克搬空,人们挤到小岛上整夜狂欢。以野外的凛风、摇滚乐和啤酒作为燃料,到12月8日列侬的忌日这束光才堪堪熄灭。
雷克雅未克的屋子大多平矮,不跨越5层。只要天色暗下来,那束光就是我的灯塔。它总是不分昼夜地在那里,安静地、忠诚地,像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有时刻夜里我走的晕了,瞥见它就能很快鉴别方位。
深夜我站在空旷的荒地里,周围空空没有阻碍,便能看到那束光最完整的样子。三束并作一束的蓝光,从对岸海平面上的一个点出发,我仰起脖子直到后脑勺和颈部的皮肤贴在一起,直到感应喉咙处的呼吸有些哽住时,才气看到它的终点。
通常,它止于一片云,一片流动的云。北欧的天是整片漆黑的,只有那一小片云在极高处以可见的速率流淌着。这使我感应心安,为很远处有一片云同我一样,同天下上许多人一样,居无定所,细微伶仃。
在厥后逐日长达20个小时的漫长黑夜里,它常是我走夜路时唯一的同伴。
六
冰岛南部的Vestmannaeyjar,“西人群岛”,15个岛屿均形成于海底火山爆发。主岛上有着不到5000的常住人口,残留着上世纪70年代那次火山大喷发的遗迹。
我去时正好遇上十月的风暴,风速13m/s,连带着暴雨一起刮断了路边的树。我和couchsurfing的host一起被关在家里一整天。待到第三日风暴稍微平息了些,我便准备背包出门爬火山。
火山离host家很近,走过3个街口就是山脚下。虽说有为游人设计的旅行步道,但只能凭据前人踩过的痕迹来判断门路。起先我还能委曲分辨出那里是路,可越往山顶走,苔原越是杂乱生长,脚下的路也逐渐和玄色的山体融为一体,让我辨不清偏向。
当我转过一个弯道,看到远处冷落地斜立着一个三米多高的十字架时,一切都最先变得魔幻起来。
整座山空空荡荡,我这一路上来竟一个人也没有遇见。没有人,也没有动物,唯一可见的活物是远处青黄的苔原。地面上散落着颜色鲜艳、形状怪异的火山石,在玄色的火山灰上显得异常耀眼。风依然凶猛,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耳朵里灌了风,生疼。
我胡乱在这座寂静的火山上行走,越走越接近海。风不停从背后推着我走向悬崖边,我险些要站不稳。既不能逆着风往回走,也做不到站直不动——只有半跪在地上时才气平衡重心。
我最先感应恐惧。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无望的行走。没有舆图,没有偏向,看不见终点,也不能转头。只能怀着恐惧,一个人不停地走着。我甚至不敢奔跑,一步步行走能给人兢兢业业的平安感,由于奔跑经常意味着一场追逐,意味着敌对、感动和忙乱。
小心地走过靠海的这一段,风逐渐变弱,至少我可以正常地行走,耳朵也不疼了。小镇重新出现在视线内,偶然也有运货的卡车从我身边开过。似乎,得救了。
当我重新踏到柏油马路上时,竟有重回人世间的感受。
我想起在冰岛景点经常看到的这些牌子。它们以“Missing”为题目,排列着两三个年轻人的名字和一些日期。
它们是无坟的墓碑,是没有情节的故事书。看到这些牌子时,我总被强烈的绝望裹挟,忍不住去想他们是怎样的两个青年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为何来到这里,那时做了怎样的选择,最后又消逝于那边?
我似乎回到2007年8月1日,看着他们的背影消逝在最远的转角处,他们还交谈着调笑着,浑然不知自己即将承接的伟大运气正从山坡上滚下来,就要落到他们头顶。最终,无措地迎接运气。
七
在冰岛,我的房间窗外是一片海。每次透过窗户看它,便想起三岛由纪夫写屋顶上的镀金铜凤凰,“其余鸟在空间飞翔,这只金凤凰则睁开光灿灿的双翅,永远在时间中飞翔……” 海也是这样逾越时间的存在。几万年前的人类看到的,与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片海景。
巧妙地,由于这片稳定的海景,21世纪的我和远古的人类具有了相同的视觉记忆。这种玄妙的毗邻感让我舍不得移开眼光。
因此我总是盯着海发呆。也不想什么,就只是看着它。
海在时间里永垂不朽,而我在这时间的永恒性眼前感应自身的细微。就算我再恒久地盯着它,对它来说也不外一瞬而已。
我看着海平线,茫然地,惊惶地,镇静地,伶仃地,困于一种凝固的状态,身体僵硬着无法转动。空调吐气的声音,冰箱电流的声音,脚趾摩擦袜子的声音,异常敏感地传入耳朵。似乎整个房间和我一起阻滞了。温热的空气不再流动,而是结成凝胶状停在半空。我盯着一个点,很久很久,直到周围的一切都变样,它们浮动起来,从固体转换成液体的状态,又像风一样流动着。
若是时间再久一点,我想我会永恒地凝固在这里,酿成一块貌寝的石头。或许我顽强地以为,凝固如雕像是恒久不消亡的体现,如金凤凰在时间里永远飞翔。
它是不动的,也是自由的。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山月入海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0515/1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