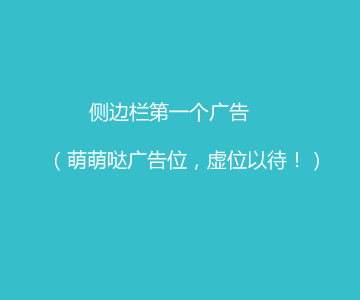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维舟,头图来自:IC photo
在现代社会,每当有全局性、高风险的灾难发作,人们总是会关注国家政府的行为。德国学者安德烈·扬库(AndreaJanku)曾在剖析一系列事宜后得出结论:若是一个政权没有行之有用的赈灾政策,便会直接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持久性。
然而,这首先就意味着人们要对政府抱有这样的期望,而在许多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大致都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看待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荒。即便在欧洲,也是直到近代,频仍泛起的重大灾难和逐步高涨的纳税人权力意识同步,才迫使政府负担起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责。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显得相当早熟。只管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一般性灾情时也通常以下层社会的自我施救为主,除非特大灾情消弭了民间所有的救灾能力,但总得来说,从极早的年月起,国家就在赈灾中饰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对应着中国人对“天”的伦理期待:国家和天子作为“天”的代表,应当、也必须饰演好拯救者的角色。
这些国家层面的实践履历,甚至比近代欧洲更早,乍看起来似乎是相当“现代”的,也因此使法国学者魏丕信深感兴趣。1973年,他发现了清代官员方观承撰写的《赈纪》一书,其中对1743~1744年间直隶大饥荒官方施救流动的翔实纪录,清楚地证明了清代权要体制在赈灾流动中的效率和有用协调能力。
在此,主要的不是这些灾难自己,而是若何应对灾难——换言之,正是在这样的极端事宜中,体现出政府对自身角色的认定,以及它能否展现出组织、效率、灵活性和稳定性,最终,正是这些反映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来说,威胁最大的两种灾难就是洪灾与旱灾。洪灾具有发作的突然性与损坏性,但在水土流失尚不严重的年月,它的连续时间通常不长,局限也不会太广,要忧郁的经常倒是灾后的疫病盛行;旱灾则相反,对水利之外的基础设施损坏有限,也并不突然,但却有可能连续长达数月、数年,波及数省甚至更广的局限,而等到人们陷入逆境时,甚至已经来不及施救,造成的社会影响之深远往往大大跨越洪灾。这就是为什么向来的官府都更注重对旱灾的救援,相关的组织流动也远为精致、有用。
魏丕信已经相当清晰、理性地梳理了清代权要体制在救荒时的种种行动:若何阻止跨地域的流民潮、若何组织粮食救援,而在发放食物时,又若何按需求水平来划分灾民的受灾水平,尽可能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国家干预,势必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影响,由于直接干预就意味着国家成了底层农民的庇护人,而这就会潜在地激励佃农的抗租行为,损害当地士绅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又不得不激励这些“士绅”拯救灾民的善举,由于在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和警力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有限干预才是可取的做法。
对这些士绅来说,和国家互助也是最可取的,由于若是社会的秩序崩塌,他们将比国家遭到更快更致命的打击。
《18世纪中国的权要与荒政》,(法) 魏丕信 / 著,徐建青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5月
这些都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体的庞大处境:虽然国家权力在理论上是万能的,但妥协是现实中明智的做法,由于负担起所有职责是不堪重负的,而且民间的自救由于不需要那么多权要层级,往往也更为迅速实时。
另一方面,虽然士绅看上去代表着社会气力,但实在他们也同样“习惯于从国家角度思考问题”——值得弥补的是,这既可能是由于儒家看法深入人心,也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从“公”的名义出发,才气将自己的“私”利予以合法化。
对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则是保持两者的玄妙平衡与整体一致,确保那些社会自组织的施救气力被纳入官方的轨道,而不至于成为挑战自身的自觉组织。
在这方面,清代政府可说相当乐成。只管在1820年后,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和治理水平的下降,直接干预能力也转弱,但它仍然乐成地让士绅负担起了职责,而无须向他们让渡权力。不仅云云,事实上是国家气力在救灾中更进一步向下渗透,逐渐接受了地方精英的墟落控制权。
一般来说,朝廷的做法是予以奖励,授予功名爵位,随后认可民间的救灾行动,将之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典型的如1671年的赈灾中,嘉定、宝山等县在州里一级设立20多个粥厂拯救灾民,这本来是下层出于赈灾治理的需要而自觉发生的组织,但随着救灾成为经常性的社会事务,这些组织也常态化,到乾隆末年,越来越多的州里公务被“厂”接受,逐渐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
直至1900年的江浙士绅的庚子救援,仍可看出这种社会自救依赖于官方认可,而且官方随时把控着干预力度和局限的自由裁量权。
作为一个仕宦数目、财政收入和发动资源都有限的前现代政府,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魏丕信以为,这是由于康乾时代的清朝体现出:
“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经有关权要机构付诸实践的相当庞大、技术性相当强的运作”。
既然云云,他很自然地以为,1820年后国家的赈灾行为每况愈下,是由于放弃了这一套一度让它乐成的制度,无论官员素质照样组织履历均泛起下降,而让位给地方精英和市场机制,却未能控制其中泛起的种种问题。
这个结论,说实话是相当令人愕然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历史的生长简直云云,但其病因却不在此。政治学家邹谠在剖析近代中国政治时,曾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断言:正是那些曾经带来乐成的因素,造成了厥后的失败。
这话在清代救灾史上,生怕也适用。简言之,当社会还相对简朴时,那一套看似周详庞大的权要体制,确实能应对好泛起的灾难;但当社会越来越庞大时,这套静态的制度就会逐渐难以应对不停涌现的问题,而此时,正由于它原先太乐成了,反而更难以动态调整,实现新的范式变化。
要明白这一点,生怕有需要先超出清代的范围,来明白下“救灾”对国家而言事实意味着什么。在此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传统中国对“救灾”的看法和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理念有着相当玄妙而重大的差异。
我们现在大多想固然地以为,救灾最主要的固然是人民的生命财富,然而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道光三年(1823)水灾的研究发现:
“国家的荒政重济而轻救,国家对灾后赈济的划定至纤至悉,而对灾患发生时人民生命和财富的抢救则既无划定,也少行动。”
这似乎很新鲜,但实在却不难明白,由于传统中国对灾荒的重视,其基本目的并不在于“拯救生民”,而在于担忧灾荒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正因此,在详细行动上,也未必着眼于迅速有组织的施救,而注重维持社会安定,让活下来的人有生路,制止激变灾民。
这就是为什么清代历代帝王都无不强调“省刑为荒政之要著”,而沈括《梦溪笔谈》中谈到皇祐二年(1050)吴中大饥,范仲淹还宴游湖上,由于这给穷人缔造了数万生计,甚至美谈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在传统宗法社会,因灾荒而大局限迁出的流民,与户籍制度有着难以和谐的矛盾,一旦暴力图食,“流民”转变为“流寇”,将对统治造成极大威胁,这才是清代权要系统极为关注救灾的真正动因。
平心而论,这样的政治思量自有其合理性。对比一下英国的状态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点。1845~1849年间爱尔兰大饥荒时,英国财政部官员查尔斯·屈维廉下令住手拯救,理由是“制止人民习惯于依赖政府”,他在时代辩称:
“政府没有任何责任来保证粮食供应或是提高土地生产力。”
效果是灾难性的,最终80万人饿死,在爱尔兰人心目中播撒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这里棘手之处在于:政府应当负担什么职责?负担到什么水平为止?若是那时英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只愿意负担有限责任,那么清代的问题却是官府负担起了无限责任。
看起来矛盾的是,国家的行为最终造成了自己的逆境。在许多国家,宗教组织都在灾荒时饰演主要角色,但邓云特《中国救灾史》、冯柳堂《中国食粮政策史》等,却都对释教所介入的拯救只字不提,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把政府视为最终的、甚至唯一的依赖。
台湾学者黄敏枝指出,宋代由于高度集权于中央,地方财赋收入所有解送朝廷,不像唐代地方财政另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其效果,从宋代起,地方政府在度支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建设皆因地方财政拮据需要责成内陆之士绅或宗教团体来担任其事”。不难设想,这自己就削弱了地方社会的自救能力,迫使人们在面临灾荒时更依赖官府出头。
在各地相对自足的年月里,这还不至于造成大问题,但到明清时代,就越来越积重难返。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进和多余的荒地削减,整个生态环境的缓冲余地不停缩减,灾难的发生频次和局限都在升级。
在宋代以前,每当灾荒时,有时朝廷还会组织灾民去异地“就食”,但明清时往往是他处也不宽裕,而户籍制度更严,受灾人口更多,大规模灾民流动的政治风险也就更高了,只有像东北这样的少数地方还能收容灾黎。
在这些庞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系统压力逐渐累加到难以承受的境界,再加上吏治的腐蚀,因而明代在正统十四年(1449)之后,国家荒政同样渐显不力,所谓“天下多事,民始觉困”。
清代重蹈覆辙,绝不是有时的。固然,正如《天有凶年》一书注重到的,清政府“特意提倡民用仓储和民众福利自有其特殊缘故原由”,由于它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更注重将抚恤民众的“仁政”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泉源。
在“永不加赋”的祖制下,清代人口增进更快、土地开发更深入,社会经济环境的缓冲余地更小,若是政府还不注重培育民间的自觉自救气力,就更加剧了自身的逆境。
晚清时《北华喜报》就发现,灾荒经常发生在“政府忘记了自身所属的正当行动局限,从而与自己的民众举行竞争的地方”,这生怕是由于,在这些地方,民众往往都“站在齐脖深的水中”,连一阵细浪都无法抵御,这反过来又使他们更依赖国家。这样,救灾政治最终造成了一种无法脱节的“内卷化”态势:不停地麋集投入,效用却在递减,无法实现顺遂转型。
再精明有用的权要组织都无法抵抗这样不停的累积效应,一旦这累积到超出政府处置能力时,溃烂就最先了。一定的放权和市场化已经不可制止,但这往往来得太迟、做得又太少、改动又太难。到了晚清,多灾多难的年月最先了。
1876~1879年的大灾荒造成华北950万殒命。西方观察家保罗·波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府以为饥荒是不可制止的事情,是自然界运动的必然效果……换句话说,政府只是思量一旦饥荒发生了若何赈灾,而没有思量若何铲除发生饥荒的缘故原由。”
确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义务,由于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维舟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0502/16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