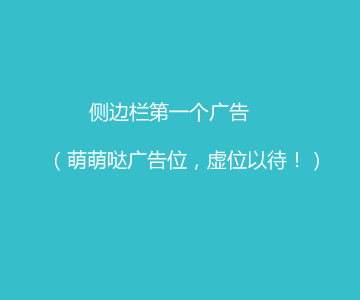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作者:于硕(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央)
受疫情影响,今年国庆境外旅游化作泡影。今天修远基金会特选编《赌城之外的澳门》一文,与读者一起纸上周游澳门。本文作者游历发现,澳门赌城虽然绚烂,但并非澳门的所有。而以往旅游团的门路走马灯似的观光赌场,未免买椟还珠。从16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澳门都是收支中国的唯一门户,是欧洲人来华的第一个落脚地,历史职位特殊。澳门数百年来都处于桥头堡的位势上,风风雨雨中也生出了怪异的夹杂文化类型。
16世纪中叶,中国文明被西方启蒙运动头脑家用来推动欧洲的世俗化,好比伏尔泰以自然神看法阐释儒家,或是莱布尼茨把“理”“太极”“天主”三者做了“三位一体”的阐释。18世纪英国使团访华, 重商主义推翻了清朝重农轻商的看法,随之而来的是鸦片战争及清朝的溃逃。20世纪发生在冷战之后,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同步。经济全球化不仅打击了欧洲——“天主死了”,也打击了中国——“孔子死了”。
本文从作者闲步澳门老城出发,从修建、文献、饮食中一窥历史的踪迹。
第一次来澳门,是在16年前,从海上逐渐靠近她,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座古老的东望洋炮台(Fortaleza da Guia),让我激动地以为正在走进500年前中欧重逢的历史原点。这次来澳门是在夜晚,在幽深迷茫的海上航行了半个多小时,一抬头满眼金光四射,横亘成墙的摩天大厦筑起一座金山金城。转变云云惊人,让我联想到曾经从飞机上看到的拉斯维加斯城绚烂的金沙金盘。
不知道澳门管理者是否想到“赌城”炫富的外墙在喧宾夺主,遮蔽了澳门幽深的石板小径和价值千金的巴洛克格调;不知道游客中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整个欧洲民族国家、宗教派系、财富探险家争斗的大舞台,上演了无数迷离幻化但却对中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剧目。这是我到达澳门时的感伤。
澳门城与澳门学
半年前也曾来过一次澳门,在香港买船票时,有人问我:“去赌场吗?”
“赌城”这个澳门的象征符号真是主导性的。“不去赌场,去查澳门的历史资料,看澳门老城。”我在为澳门打抱不平。以是,第一次造访澳门的人要快速穿越门脸上的款项符号,进入老城的文化要地。
整个老城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划定为人类文化遗产,这在中国是唯一的,其他进入名录的大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修建,而澳门城保留了整体的空间布局,使我们得以“回到历史现场”,重构那时人们的生涯天下和时空人际关系。这可以让我们想象都会若何运转,妈阁庙的进香人是否随后又去了天主教的花王堂?
人文游客除了在老城里溜达,还可以在她众多汪洋的资料中探幽寻微,熟悉这个发生过中欧重逢大历史的小城。澳门城很小,吴重庆教授讲的故事很有趣,他在中山市崖口村做观察,崖口村的书记告诉他“崖口村的面积有13个澳门大”。从中可以解读的是,虽然没谁听说过崖口,但那是改变生态的围海造地的人造村,其中不乏中国式的好大情结。
走遍小澳门很容易,站在东望洋炮台高处,整个都会一览无余。但进入细节去体味都会的风范和历史的秘闻则需要时间,而在细节中,我们发现了多元文化的在场和跨文化的创新。不妨让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街道的名字都是用“葡式”瓷砖做的,我们自然也会想到明代青花,想到地中海周边的都会,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尔,北非的突尼斯……我们由此联想到宋代以来的海上商业,想要探讨明代青花与阿拉伯花纹的关系,再想到占领欧洲伊利比亚半岛达800年的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及其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同样有趣的是在议事厅前地,低头见到的是全球著名的巴西象征——Copacabana海滩上的葡式瓷砖波纹,于是,里斯本—澳门—里约就在这统一符号中象征性地连结起来。
我们经由许多老修建,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庙宇和闽南的民宅阁楼,伊斯兰—印度气概的军营,但更多的是巴洛克式、新古典式的教堂、学校、住宅、公共机构,使我们感应置身于欧洲南部的某个小城,只不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亚洲面貌居多。澳门都会化似乎是里斯本的复制,笔者一下就联想到大教堂所在地的瑟区(freguesia de Sé)。
事实上,直到1999年之前,澳门另有隶属葡萄牙政府统领的7个下层行政区,叫“堂区”(freguesia),人口统计、政令运作以此为单元,好比大堂区、风顺堂区、花王堂区……两个都会都是海岸丘陵地带,骑自行车很难题,慢节奏的步行则更能感受其粘稠的平民气息。它们都属亚热带气候,散发出的气息令人模糊,不知身在那边。
澳门城需要深入阅读,由于她厚重而尖锐,爱恨交集,悠久多元,蕴藉而轻盈。被彰显的那些浅表征象,不及她的精湛之处。我给人人推荐一本阅读都会的书,叫《看不见的都会》(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著)。书中以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对话为主线,描画出林林总总真实的、想象的、绚烂的、颓败的、轻盈的、欲望的、符号的、隐藏的、空中的都会。马可波罗从外部形貌了一系列的都会型构之后说:
至高无上的忽必烈汗……组成一个都会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宜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往返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劈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若何披红挂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男人若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若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泛起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若何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若何坐在码头上一面补网,一面重复着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里被遗弃在码头上。都会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停涌流的影象的潮水,而且随之膨胀着。
看不见的都会
澳门城正需要从“第三度知识”,即关系型知识(G. 德勒兹)的高度上举行阅读。吴重庆先生谈过“生涯中的对话”,好比围绕蚕丝生产的交流,就是对澳门的第三度阅读。历经500年的中欧澳门交流史具有唯一性,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跨文化相互进入。在华洋杂居的“澳门人”的一样平常生涯中,在有意识的区分中,无意识地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它属于澳门的唯一性。也许我们可以说巴西有类似之处,但澳门没有像里约热内卢那样有成批的葡萄牙移民,里约没有中国天子—罗马教宗—各新兴主权国家—岭南文化—释道儒合流等因素组成的错综庞大的交织场。
我上一次脱离澳门的时刻,带走了许多书和文献复印资料,其中有老友吴志良和汤开建、金国平教授主编的六卷本《澳门编年史》。这是一套绝无仅有的史书,编辑角度怪异新颖,以一年为段线,远大与细小的事宜并行收录,接纳中国和欧洲(主要是葡萄牙文)的文献。我以为这是有关文艺复兴末期以来,中欧交通史最丰满有趣的史料索引,是研究者必备之书。让我兴奋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这部编年史的“直接性”极具吸引力,自己险些就是新史学的“第一手资料”。与传统的编年史差别,六卷本体现了新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三个新的向度:a.自下而上,b.平民生涯,c.主位陈述;拥有得天独厚的多元史料类型:老城、修建、墓地、绘画、器物、航海纪录、关税收条、教会生死及婚礼簿、政令、商业文书、报刊、通讯、条记、冒险家随笔、《澳门纪略》一类地方大员的亲历记、县志、回忆录……
若是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E.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的作者明白中文,或者微观史学大师、《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的作者C. 金斯堡见到这一编年史,一定会做出惊世骇俗的阐释。
第二个理由是,虽然《澳门编年史》绝无仅有,厚实新颖,但还很缺少其他欧洲语言的资料,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厥后的英文等。好比法文资料十分主要,由于17~19两个多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等)在澳门扮演了与葡萄牙分庭抗礼的角色,指令直接来自两个对立体:梵蒂冈教宗和法国国王,悖论地交杂着宗教的和主权国家的使命。
仅仅是外方传教会与澳门相关的文献就许多,整理翻译它们已然是一个世代工程。从我本人的研究兴趣和语言能力而言,我希望可以为此项工程作出微薄的孝敬。由于不弥补这一部门资料,就不能完全呈现在澳门上演的近代欧洲世俗化、主权化、全球化的春秋争霸剧,也不能明白各国与清帝国朝廷的往来关系。因此,少年澳门学(macaology)任重道远,生命力无限。
阅读一个都会,于是就成为一种存在哲学的探微。老友陈越光先生提到人类文明的突变和逾越,提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史华兹将这种逾越的一个主要条件称为“小我私家退而远瞻”。退居澳门的研究,在疑心彷徨的今天,或许可以成为大历史逾越的一种头脑和知识资源。
细节中的大历史
澳门研究,得天独厚的是拥有其历史现场。听钟声涛声,闻酒香花香,望千帆竞渡,观城池楼宇,自下而上,从现实空间进入它的文字历史。而这一切都需要从生计体验出发,在细节上下功夫,从而对种种文化内部的张力和人们跨文化的创造力保持高度的体验性和敏锐性。
笔者自己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进入澳门,从以天下为家的流浪者的亲自体验,想象澳门的建城史:可能出于一种空间的相似感,使第一批葡萄牙水手们决定在澳门半岛停泊。在众多的大海中经由生死搏斗,疾病疲劳,海盗追杀,突然感应生命的极限和艰辛;而这个“有时”邂逅之地,可能是自己原来生计空间的表示,一种求同的亲和性:移民者会在远离河山时加倍重构自己的已往,云云找到乡愁的载体和慰藉。
这种征象许多,希腊人在法国确立的第一个都会是马赛,异常像雅典。澳门让我以为异常像里斯本。也许我们还可以沿着历史文献的线索追踪这种可能性:为什么是澳门而非别处?有一个小的历史细节,151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船先到了香港的屯门,但很快就(被迫?)脱离了。若是他们那时留在了香港,若何会有厥后的英国占领和鸦片战争及厥后的英帝国统治?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让我们想象,好比那时的“唐人”和“弗朗机”人在澳门若何相处?
城墙:16世纪中叶,澳门城最先兴建。城墙具有平安防御、凝聚整合的功效。围绕澳门城墙,在明朝政府、澳门殖民者及荷兰后起之秀之间,连续几个世纪争执拉锯。澳葡建城,明清拆毁,以“防夷坐大”,“自成一国”。澳葡则随拆随修,直到1879年自动拆除,以显示其自由商城。其中还要加上与荷兰的战争,以是,澳门城墙的符号意义值得细细探讨。
照明:澳门的照明系统像在任何一个区域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改变了人类在自然光下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关系。澳门的照明系统经了三个阶段:烛灯—油灯—电灯。其间的变迁,充满了都会治安及公共伦理、国家利益竞争和现代化的生涯方式的打击,给我们许多启示。一最先,澳门华人晚上出门必须提着灯笼照明。1847年议事会(Leal Senado)让住民将灯笼挂在自己家门口,由自照酿成公共照明,这是都会公共空间意识的最初体现。1849年,葡萄牙女王批准颁行澳门照明章程,不再强制晚上提灯笼行走。这时代蜡烛或火水油(石油)并用。
1904年,澳门最先使用电灯,引起许多争论,第一是使用权力,谁有权力享受这些电灯。最早在葡萄牙人区安装,厥后才逐步扩展到原住民区,体现了认同上的区分机制。第二是商业利益,各国公司介入了竞争。第三是看法冲突,反对者强调其虚耗,晚上就该睡觉,安乐电灯,有伤风化;澳门台风频仍,不适合安装等等。可恰恰是电灯的装置,改变了石龙关系,使生涯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日落以后的时间可以继续生产,现代夜生涯在灯光下登场。
澳门菜:怪异土生的澳门菜系(macaense)是一种跨文化的创意。澳门菜融合了葡萄牙和中国南部烹饪,并受到巴西、印度及其他东南亚美食的重大影响。从东方的香料夹杂,包罗姜黄,椰子汁,肉桂等,到欧洲菜肴的配料和调味,通过烤和焙烧,别开生面。最盛行的小吃是猪扒包,甜品有姜撞奶,葡式蛋挞,杏仁饼。民以食为天!
中欧重逢的中央舞台
从16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澳门都是收支中国的唯一门户,因此成了欧洲人来华的第一个落脚地,历史职位特殊。他们在这儿守候中国政府的签证,或者没有签证但守候悄悄潜入的机遇。他们守候每月两次的通商机遇,与“珠江上的人”举行商业商业,这是他们唯一能跟中国人买卖的机遇。现在的广州买卖会也许就是从那时最先的。他们也在这里守候着搭乘返回欧洲的船只。澳门数百年来都处于桥头堡的位势上,风风雨雨中也生出了怪异的夹杂文化类型。
以是,澳门学不单单是资料搜集,或像许多人说的,旨在研究改善中国与天下的外交关系。澳门学一定是三个远大的历史交织场中文明的融合、个体的重逢和对话。中欧之间的三次重逢,这是十多年前我在博士论文中提炼的观点,并试图在中欧社会论坛的运作中举行第四次重逢的理想型实验。
三次重逢的第一次发生于16世纪中叶,始于澳门,并使澳门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欧重逢的焦点舞台,也是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相互争霸的主要舞台。三次重逢中,澳门都扮演着异常主要的角色。不外,1833年葡萄牙语梵蒂冈交恶,保教权旁落法国,1842年鸦片战争后香港开埠,英国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澳门东面78公里的制海权,澳门的焦点职位逐渐被香港取代,在庞大的历史交织场中有所失势。1854年,法国遣使会神父(E. R. Huc)古伯察这样形貌澳门:
今天,澳门剩下的只有回忆,英国在香港开埠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古老优美的楼宇空置在那里,没有租客,可能几年之后,欧洲船舶再经由这个葡萄牙曾引为自豪的富有的殖民半岛时,看到的将只是裸露的岩石,在浪涛拍打中无限凄楚和凄凉,几其中国渔民会在黑黝黝的礁石上晒他们的渔网。不外,传教士会喜欢来凭吊这些废墟,由于澳门的名字将永远载入福音流传的史册。几个世纪以来,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培养了许多去中国、日本、鞑靼、韩国、交趾支那和东京流传福音的使徒。
我们把谁人时代的人类称为“神贤人”,由于他们是敬畏神灵的,因此中欧双方的争执主题是,人格化的天主和宇宙太极的“天”孰高孰低。人们关切的是永恒的精神性和短暂的世俗性之间的关系。信仰作为一种个体内敛的精神行为尚存,而理性在那时还带有探求真理的神圣性,以是,这次重逢是一次精神看法的重逢。重逢的地点在中国,受震撼最大的却是欧洲。中国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被启蒙运动头脑家用来推动欧洲的世俗化历程。我们看到,莱布尼茨把“理”“太极”“天主”三者做了“三位一体”的阐释;伏尔泰以自己的自然神看法阐释儒家;洪堡在语言和国民精神之间搭建同构性。基督教在中国部门文人那里也引起了相似的主观阐释。
中欧第二次重逢——“英雄人”重逢。第二次重逢在差别的历史场域中发生,以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勋爵(Macartney)使团访华为标志,止于20世纪中叶。起点仍然是澳门。在通常的表述中,这段历史的主导象征符号是鸦片战争,中华帝国遭受蹂躏与蹂躏、丧权辱国。一方是西欧殖民主义的野心扩张和武力护卫的重商主义,一方是拒绝通商的华夷朝贡系统,最终是天朝的溃逃。我们在此需要梳理的是,在这“页页都是血泪史”的历史影象中,同时另有另一个很少被言说但却相与随同的历史,即个体之间的人与人重逢的历史和中国与天下同步的现代化历史。
这次重逢的历史性体现在民族主权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宗教气力的淡化并在相当意义上成为国家竞争的工具。欧洲刚刚完成她的一系列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头脑启蒙,今后确立了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绝对理性、国际规则,在全天下眼前以典型自居。西欧以自由商业为名,在炮舰随同下推行扩张的外交政策,并将殖民扩张视为国家的权力和文明的提高, 一种“保证人类幸福”的福祉。这一全球化历程将在200年后把天下酿成统一市场。
第二次重逢发生在西方的中国观泛起逆转的时期,由赞美中国向鄙夷中国转向。新生的各“民族国家”袍笏登场,在天下舞台上摆出主角姿态,并相互间通过较量确立平衡关系。鸦片战争的“理由”和租界的设立都反映了这种“主权国家”的新型关系。而保持华夷贡奉系统的中国人继续显示出一直以来的对“商”的蔑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接受传教士所流传的头脑好像比合理商业中的商品更容易。这在澳门历史中有许多显示。中国被迫进入天下系统和现代化历程,决意向“敌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重逢推促着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他我认同”(hétéro-identité)的时期,并在自卑和自尊之间尴尬地倘佯,直到今天。
中欧第三次重逢——“经济人” 重逢。第三次重逢发生在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30年冷战之后,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同步。这一历史人人都熟悉,但在评价上存在着许多分歧,由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一切重逢都必定是全球性的,“中欧重逢”都是全球重逢(这固然不故障中欧之间的详细联系)。若是从精神性状态上判断,从第一次重逢最先,人类历史履历了一个下行的历程:“天主死了”(尼采),“孔子死了”(刘黑马),人成为天下的主宰,也贪图成为自然的主宰,肆无忌惮地破坏蹂躏着地球家园。人类的谵妄依凭的是量化的尺度,精神性退却,伦理溃不成军。
从澳门最先第四次重逢
在构想第四次重逢之前,我在这里先归纳在澳门共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三个历史交织场。
第一个历史交织场是近代欧洲各主权国家争霸天下的庞大场,澳门是一个大舞台,但清廷仕宦如澳门同知、香山知县甚至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经常只是台下看客,主角是欧洲各国兼有圣俗双重使命的神职人员,成就了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事业。
第二个历史交织场是明帝国闭关锁国和欧洲新大陆开发张力中的中欧相遇场。没有澳门的中介,就没有中国和欧洲的接触,明代作为中华文明最绚烂的时期而自命为天下唯一的中央,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活力也使她自名为天下的唯一中央,两个“唯一”中央在中央之外——澳门汇合。功效之一就是启蒙运动头脑家吸收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把汉代“陈平平民为相”当成同等选拔精英的楷模,确立了那些至今仍声名卓著的名校Grandes Ecoles;中国成为欧洲理性主义的捏词,介入了近代世俗化的历程。
第三个历史交织场是澳门自身生涯天下的跨文化场。澳门像一个炼丹炉,种种文化、头脑、利益阶级都被集中于此。认同意识是一回事,融合了的表征符号是另一回事,天长日久,澳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礼仪符号,形成了怪异的生涯方式,缔造自己特有的跨文化性。这个跨文化性的乐成具有方式上的借鉴意义,更有信心上的激励性:差别文化的人可以相互接受,共同生涯,人类共同体是可能的。
澳门学因此就担负着一小我私家类使命:梳理提炼人类共生的履历:若何化误解为明白,化敌对为互助,化腐朽为神奇。
在跨文化的履历中,我们设想第四次重逢——“生态人的重逢”。第四次重逢的智慧之光早在40年前就开启了,以罗马俱乐部1972年揭晓的《增进的极限》为标志。讲述揭晓时曾引起过猛烈的指斥,耶鲁经济学家华利克在《新闻周刊》中将其说成是“不负责任的一派胡言”,是哗众取宠的夸张,没有正确的科学盘算。
40年后的今天,在灾难眼前,人们才认可该讲述的先见之明,地球简直显现出来自然极限。那时只是一些先知先觉的小我私家在披荆斩棘。20年前则已集结成军,标志是1992年的里约地球岑岭集会,是罗马俱乐部的新书《逾越极限》。今天在灾难席卷全球的危急眼前,在无力感笼罩人类的悲情中,去年的里约 20岑岭集会泛起公民社会的总动员:“生态人”期望逾越人类社会、制度、文化、种族的界线,联合起来,与大自然重归于好。
在大都市和权力中央被旧有的头脑模式和利益集团严密掌控时,澳门这块海角飞地正可以成为生态时代的实验中央,一个头脑融会贯通的炼丹炉,一个生态人的落脚点和起点。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修远基金会(ID:xiuyuanjijinhui),作者:于硕(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央)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1004/3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