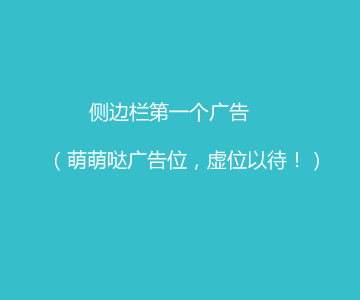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护vs鹏(ID:pengpengidy),作者:鹏鹏,题图来自:《疯狂麦克斯4》剧照
1968年,人类被一场死亡瘟疫消灭殆尽。瘟疫的受害者都变成了吸血鬼复活;地球上的最后一人如果想要幸存下来,他必须杀尽这些吸血鬼。
1997年,导弹防御计算机有了自我意识,并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挑起了一场核战争。30亿人死于非命。幸存者们把这场原子烈火称为审判日战争。
1999年,一名黑客发现那一年根本不是1999年——那一年是更遥远的未来,而且他的思想被困在了一个由机器建造的虚拟现实空间里,机器让人类相信他们是自由的,其实只是为了哄骗他们成为奴隶。
到了2020年,这些黑暗的未来一个都没有发生——至少还未发生。但科幻迷们已经在大银幕上统统经历过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把可能的未来描绘得梦魇一般,一直都是科幻电影中最为流行的手法之一。传统观点通常都是这样假定的,好莱坞电影只涉及逃避现实的题材。
然而,制片厂继续出品那些明摆着不会盈利的故事,而观众对它们的追捧也从未停止过,这好像有违直觉。这些影片并没有试图让我们逃避烦恼,在90分钟或者更长的这段时间里,它们却把我们困在了那些可能发生的、最黑暗的未来当中。
《我是传奇》2007年改编版电影海报
最早的几个例子改编自小说《我是传奇》,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后启示录小说的普及之作。麦瑟森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54年,是一个增添了科幻色彩的经典的吸血鬼故事:致命的疾病席卷了全球,把感染者都变成了吸血怪物。侥幸存活的最后一人名叫罗伯特·内维尔,他天生对那种病毒有免疫力。白天,内维尔四处搜寻生活供给品,并试图找到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夜晚,他给他家周围布满工事,以防止那些不死生物的军团冲进来杀掉他。
麦瑟森的书曾三次被正式改编成电影,每部电影都对原作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最贴近小说原作思想的(也是其中预算最低的)一部是1964年的《地球最后一人》,文森特·普莱斯扮演了人类唯一的幸存者(在这个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是罗伯特·摩根)。
七年后,查尔顿·赫斯顿主演了电影《最后一个人》;这一次,人类是被生物武器消灭掉的,赫斯顿扮演的内维尔猎杀的也不再是吸血鬼,而是一个被称为家族的白化突变者的邪教组织。继海斯顿之后,又过了大约35年,威尔·史密斯在第一次沿用原作书名的改编电影《我是传奇》中扮演了内维尔这个角色;这次的诠释是由弗朗西斯·劳伦斯执导的,内维尔在荒芜的纽约城里四处游荡,同时与夜魔进行着一场战争,这些怪物同时拥有前两部电影中的吸血鬼和突变者两者的特质。
根据麦瑟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各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但三部都源自同一个黑暗幻想,讲述了在一片无法无天的废墟上所上演的迂回和挣扎。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麦瑟森的书和那些受它启发逐渐流行起来的小说都很像西部片,这种类型片所聚焦的主人公一般都是独自在一片未开化的荒蛮之地上伸张正义,它们开始与时代精神渐行渐远。
这就好像是对那个由粗犷、暴力的个人主义所主导的“更简单”的过去的怀旧式反思,只不过被对未来的憧憬所取代,而这个未来历经浩劫又重新变成了野蛮的西部世界。在那个地方,那些同样的价值观又可以回来了。正如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所言,21世纪的“幻想的精髓”是后启示录幻想的一种翻版:“你,你的汽车,和你的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是传奇》的各种不同电影版本就是这种幻想精髓的样本。
罪犯克星“机械战警”1987年电影海报
如果说这种幻想是从麦瑟森的小说中起源的,那么在《疯狂麦克斯》系列电影中可以说到达了它的巅峰,导演乔治·米勒的这个四部曲,用了40年的时间让这个未来之旅逐渐陷入了疯狂与无政府状态之中。影片《疯狂麦克斯》发行于1979年,片中时间被设定为“距今几年之后”,主线围绕即将分崩离析的澳大利亚的一位公路巡警麦克斯·罗克坦斯基(梅尔·吉布森饰)展开。
在1981年的续集《公路战士》中,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已不复存在,麦克斯无意中拯救了一小群受凶残歹徒攻击的定居者的救星,这样的故事类似于约翰·福特的西部片。
接下来在1985年的《疯狂麦克斯3》中,麦克斯与一个名为巴特敦的沙漠村落里的一伙角斗士纠缠在了一起。30年后的2015年,米勒又带着《疯狂麦克斯4:狂暴之路》重回这个系列,电影中的麦克斯(如今的扮演者是汤姆·哈迪)流浪在一个甚至被破坏得更加严重的未来世界里,他邂逅了一个由女人组成的反抗组织,她们的敌人是一个名叫不死老乔(休·基斯-拜恩饰)的可怕独裁者。
宛如时尚大片的《疯狂麦克斯4》
《疯狂麦克斯》中社会被破坏的程度是逐渐加剧的:每部电影都放大了制作电影那个特定时期的焦虑。制作《公路战士》时,正值1979年能源危机的觉醒,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这个星球上自然资源的枯竭程度日益严重的担忧;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出现在新闻里,《疯狂麦克斯:狂暴之路》想象出了这样一种未来,那时的水资源变成了地球上最珍贵的东西。
总体上说,《疯狂麦克斯》系列电影把未来描绘成了一幅黯淡的图景,但又不无希望。这正是这些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疯狂麦克斯4:狂暴之路》的结尾,麦克斯的女性同盟——她们由坚强的大将军弗瑞奥萨(查理兹·塞隆饰)领导——取代了不死老乔在他那个部落中的首领地位,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世界末日”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事实上,重生一直是黑暗未来电影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复活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机械战警》(RoboCop,1987)中,底特律在不久的某个未来濒临混乱的边缘。为了便于建设他们的三角洲城市开发项目,全能消费品公司(Omni Consumer Products ,简称OCP)控制了当地的警察部门,开始用机器人来代替人类警察。他们复活了一个名叫墨菲(彼得·威勒饰)的警官,把他变成了机械战警,他的程序被设定为保护无辜者,以及OCP公司的老板——而OCP公司之外的人对此毫不知情。但公司高层并没有算计到机械战警还保有他生前作为墨菲时的记忆,也没有料到他最后会重获人性。
导演保罗·范霍文的这一版《机械战警》,讲的是一个被不负责任的公司所控制的未来,是将里根经济学鼓励贪婪的那个时代推演到极致的结果。这部电影对人类的看法也同样愤世嫉俗。在机械战警第一次巡逻底特律街头时,他救出了一位受几个暴徒攻击的妇女,暴徒们是在一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实施犯罪的,广告牌上写的是:“底特律城:未来有一线希望。”这个广告牌在整部电影中反复出现,但它四周的未来世界显然没有一丝希望——只有悲惨、衰败和剥削。
《机械战警》只是众多黑暗未来电影中的一部,在这些电影中,人类和机器总是以某种荒诞的方式掺和在一起。其中,反乌托邦电影的名单上要是没了《银翼杀手》就不能算完整了,雷德利·斯科特的这部标志性的黑色未来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警探(哈里森·福特饰),他的工作就是猎杀“复制人”——一种与真正人类难以区分的人造生命体——地点是2019年环境严重恶化的洛杉矶市。在《银翼杀手》的未来世界里,阳光不再照耀,雨水从不停歇。哈里森·福特扮演的瑞克·戴克是退休后重被任用的,目标是捕杀一群逃亡的复制人,他们返回地球的目的是找到他们的制造者,希望从他那里能延长他们有限的四年寿命。
除了拥有惊人的力气之外,复制人类与普通人类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身上能表现出人类特质的可能性,引发了关于他们存在的本质的伦理学和哲学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泰瑞公司的奴隶,是这个公司把他们造出来的,与机械战警是OCP公司的奴隶的情况非常类似。
《黑客帝国》(1999)的中心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奴隶制。我们初次见到尼奥(基努·里维斯饰)时,他过着卑微的电脑程序员生活。从尼奥接到墨菲斯(劳伦斯·菲什伯恩饰)打来的神秘电话的那一天起,一切都改变了。他把真相告诉了尼奥:经过一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大战后,机器开始收割人类身体里的生物能。尼奥原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台高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设计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保持顺从,并且察觉不到自身被利用作一种巨型肉体电池这一事实。
至今无法超越的《黑客帝国》
尼奥的发现成了他最糟的噩梦——但对每一个动作片影迷来说,却美梦成真了。那个计算机矩阵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因此尼奥和他的同伴们只要不断增强与计算机程序进行对抗的能力,就能改变那里面的规则。敲击一下键盘就学会了功夫,也使编剧兼导演的拉娜·沃卓斯基和莉莉·沃卓斯基能把《黑客帝国》与身体对抗的打斗和追逐镜头打包在了一起。
当电影在1999年发行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些特效——特别是那种结合了超慢镜头与环形镜头移动,被称为“子弹时间”的技术——变得轰动一时,彻底影响了整整一代好莱坞大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码技术也把深藏于影片核心的一个有趣的矛盾暴露了出来:《黑客帝国》在深刻怀疑技术的同时,也在完全依赖着技术。
还是一名程序员的时候,尼奥相信他能利用电脑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进入了黑客帝国之后,真相却是反过来的;机器正在利用人类来巩固它们的生存。当沃卓斯基姐妹(当时还是兄弟)在1999年把这些创意推出来的时候,社会好像正处于一个令人激动的新数字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几乎过了20年以后,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纳了那个数码世界,许多人为此感到担忧,与此同时,沃卓斯基姐妹当年对大众会被这种技术所奴役的恐惧,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共鸣。(好奇一问,在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停下来了几次去看手机?)
尽管《黑客帝国》在那个虚拟世界中所设置的各个背景,看起来像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或21世纪初期,影片中的故事实际上是发生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后。当尼奥和他的同伴们在惨淡的“真实世界”和光鲜的虚拟都市景观之间出出进进时,这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穿越时空的旅行,这是致敬另一种极为流行的科幻类型片:人们进行时间旅行的冒险,从未来回到过去,为的是从根本上阻止黑暗未来的到来。这样的电影有很多——《十二猴子》(1995)、《环形使者》(2012)、《明日边缘》(Edge of Tomorrow,2014)——但最有影响力的还要属詹姆斯·卡梅隆的《终结者》和《终结者2:审判日》。
《终结者》工作照
在第一部《终结者》中,一个拥有意识的电脑程序从未来派来了一个机器人(阿诺德·施瓦辛格饰),目标是杀死萨拉·康纳(琳达·汉密尔顿饰),这个女人在将来的某天会生出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又会成为人类的救星。多亏有来自未来的战士凯尔·里斯(迈克尔·比恩饰)的帮助,那个机器人失败了。在《终结者2》中,未来的机器又派来了更高级的杀手,一个液体金属机器人(罗伯特·帕特里克饰),他要杀死的对象是萨拉的儿子,还在青少年时期的约翰(爱德华·福隆饰);这一次,未来已成年的约翰重新编程了施瓦辛格那一版的机器人,并派他回来保护过去的自己。
在卡梅隆的两部《终结者》电影中,各种悖论层出不穷。约翰是萨拉和凯尔的儿子,然而在约翰派凯尔回到过去使他自己被受孕之前,他早已莫名其妙地存在了。
在续集中,来自第一部电影中那个已经被毁灭了的终结者机器人的残骸,成了开发天网计算机项目的关键,而它起初正是被天网派到1984年来的。这些时间方面的谜题就像是有趣的智力题,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传达终结者系列电影的终极信息,这个概念凯尔·里斯在第一部电影中已经明白讲出来了:“没有命运,只有我们自己创造命运。”
《黑客帝国》中,基努·里维斯躲避子弹的经典镜头
雷·布拉德伯里是多部经典科幻小说的作者,例如《华氏451》(1953)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1969),他经常喜欢说的是,他不是黑暗未来的预言者,他是黑暗未来的阻止者。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黑暗未来小说背后的动机和观点。它们绝不仅是想象出最糟糕的状况,它们是在以此来警告受众。在《终结者》和它的续集中,正是这种前瞻性的思想推动了电影的叙事。卡梅隆的电影并没有把故事放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并试图通过吓唬观众以防止它变成现实,他的电影讲的是一群积极奋斗的人们,他们正在阻击反乌托邦未来本身。
《终结者2》的结局强烈地暗示出萨拉和约翰·康纳已经阻止了审判日战争的到来,但接下来又出了4部《终结者》的续集,尤其是出品于2019年的《终结者:黑暗命运》,时隔25年之后,卡梅隆再一次参与其中,为我们讲述了新一轮黑暗未来被人与AI合力阻止的故事。阿诺德·施瓦辛格、琳达·汉密尔顿悉数回归,给足了观众惊喜。
相信我们的英雄会成功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那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觉起来也挺不错。正如萨拉·康纳在《终结者2》结尾时说的,“未知的未来向着我们袭来。”正是这个赋予了这些电影以力量:认识到末日——不管是每个人的末日,还是全社会的末日——随时都可能降临。
总会有新的东西使人害怕,但也总会有新的电影来帮助应对这些恐惧。隐隐从黑暗未来透露出的一些曙光,最终引领出绝处逢生或是力挽狂澜的结局,这种裹挟又不得不让我们过早地思考这些让人发指的议题。黑暗未来的意义大抵便是如此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护vs鹏(ID:pengpengidy),作者:鹏鹏
版权保护: 本文由 原创,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allart.com.cn//cms/2020/0620/2207.html